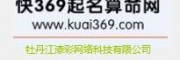李宗恩估计是最不受同门欢迎的那个人,介绍倪海厦的文章和视频里称之为“某李姓弟子”,这个李姓弟子,介绍自己是关门弟子、唯一传人、学术传承人、倪海厦指定传承人、嫡传弟子等自封头衔。
同是倪海厦弟子的林大栋,他的新作《佛州汉唐跟诊日志》序言里,写到:
关于倪师,坊间流传有太多不真实的故事,像”倪师是经方家,他从来不用任何时方“,甚或有些故事已经有了”造神运动”的倾向。更有将“倪门掌门、唯一嫡传弟子、指定学术传承人”等自创的头衔自封于一身的欺世盗名之徒。
在李宗恩的著作《当张仲景遇上史丹佛》里也可以看出李宗恩爱自吹、爱指点江山的特点。书中对钟南山的批评非常明显,对自己学习能力、医术水平的评价也非常高。
倪海厦参加《国学堂》后与梁冬、徐文兵合影
且不论李宗恩在同门中的口碑如何,李宗恩能够被斯坦福和哈佛同时录取,而且能够在能人扎堆的硅谷混得风生水起,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现将李宗恩博士纪念倪师的文章摘录如下,供各位爱好八卦的倪师爱好者共享。只做格式调整,不做任何文字修改。
原文如下:
我不是跟随倪老师最早的学生,也不是和他学习最久的学生,但或许是和他机缘最特殊的学生。我和倪老师的互动,或许也和绝大多数的学生们不一样。许多人觉得倪老师很严厉,我从来没有看过倪老师生气,许多人不敢打扰倪老师,我和他半夜在网上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许多人见到倪老师即拘谨恭敬,他却拉着我去飙车,寻求放开的自我 。
这次倪师母决定要出版倪老师过世十年的纪念文集,好几位师门下的前辈和后进联络我,希望我多聊聊我认识的倪老师。许许多多的往事,一大堆的网上对话及电邮,大多是我和倪老师的私人事情,以及彼此对许多人事物的讨论,没有什麽好公开的。不过,难得出版纪念倪老师的文集,把一些故事写下来,一方面免得老了后都忘了,另一方面让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倪老师,倒也不失文人的风雅。
李宗恩与倪海厦
大将风范
那一年,我和孟怀萦教授邀请倪老师到史丹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翻译与大陆不同)演讲,倪老师欣然答应。
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位于史丹福医学院李嘉诚中心(Li Ka Shing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enter)的场地,那已经是校内最大的演讲廰之一,可以容纳三百多人。倪老师演讲的消息还没正式公布,参与协办的台大校友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工作人员们都急着想先报名,预估参加人数会远远超过了会场的容量。我们只好寻找校外的场地,忙碌奔走后,总算订下了圣克拉拉会议中心(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的大型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即使如此,订票的数目依然超过了会场的容量,很多人得当场排队候补。
正当我忙于协调两百多位参与协助的志工朋友时,孟教授突然急着找我,她在手机那头大叫:“倪老师的投影片怎麽只有十几张!”原来倪老师把演讲的投影片发给我时,我还没来得及看,就直接转发给孟教授。她看了以后很紧张,一般而言,一张投影片讲一到两分钟,倪老师三个小时的演讲,少说也得有个七八十张投影片,怎麽只有十几张?孟教授和其他志工朋友们,没有一个敢问倪老师,只好由我来问老师。倪老师听了,气定神闲地说没问题。果然,倪老师上台后,台风稳健,侃侃而谈,根本不需要投影片。倪老师的气势让一千多位听众全神贯注,整场演讲,俨如大将挥兵前进,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为大家带来了难以忘怀、醍醐灌顶的中医启蒙教育!
倪海厦在硅谷演讲后合影
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医的传承
倪老师在旧金山湾区短暂停留期间,孟教授特别在朋友家举办一次聚会,请了好几位有影响力又对中医有兴趣的朋友们,让他们有机会向倪老师请益。
聚会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好酒好菜,每位嘉宾都很尽兴地和倪老师及其他人寒暄,一幅宾主尽欢的画面。然而,倪老师的心思似乎不在现场,中间空档时间,把我单独拉到另外一间房间,拿出一叠印好的资料,他说:“宗恩,这是我将在台北要教大家的病例,我先来跟你讲解一下…”。倪老师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解释给我听,也一一回答我的提问。其他人看到我们两个单独交谈,虽然心里急着希望倪老师返回到聚会里,也都不好意思打扰我们。就这样,倪老师和我撇下大家,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倪老师确定我完全了解那一整叠的病例,他才放心地回到餐厅,再度和大家闲聊。
倪老师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嗜好,其中一项是枪枝
倪老师有很多把手枪及长枪,除了摆在枪柜里的枪枝外,也有好几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藏在家里各个房间里。他说这样坏人闯进家里时,无论他在哪个房间里,都有办法拿到枪枝来捍卫住家。
一天傍晚,倪老师及师母找我、方亮(老师的姪子)、雅晴(诊所跟诊班长)及伊鸣(北大留英医学博士)到家里来一起共进晚餐。茶余饭后,老师和我们闲聊,我们起哄要看倪老师收藏的枪枝,老师兴高采烈地从餐厅开始,一间一间地把藏好的枪拿出来给我们看,最后还带我们到二楼主卧房,打开枪柜,拿出一把把长枪来给我们看。
方亮、雅晴及伊鸣三位对枪枝没有什么经验,特别兴奋,抢着把枪拿在手上,却没注意到枪口是不是对着人。这可把倪老师和我吓坏了,无论枪中是否有子弹,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坏习惯。我和老师四目相对,会心地点个头,两人一起把所有枪枝摆回到枪柜里,我以老师得早点休息为理由,让他们三位从兴奋中清醒,一起向老师告辞。倪老师好几次说要一起去靶场打靶,我也特意买了一副射击用的护目镜,准备在靶场给他一个惊喜。
很可惜,虽然老师和我很多次一起聊天、吃饭、飙车,就是没有一起打靶过,机缘错失了,就再也没机会了。现在,我每次去靶场打靶,都戴着当初为老师买的那副护目镜。
倪海厦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的讲座
人纪与天纪
我和倪老师学习人纪之外,老师也要我学习天纪,他很早就把一套天纪教材寄给我,我也常常向老师请教。
曾经有几年,我非常热衷于天纪,紫微斗数似乎也算得挺准。很多人知道倪老师看诊时不帮人算命,大概没几个人知道倪老师推辞不了找他算命的人情压力时,他会把人转给我,由我来帮忙算命。
有一次我在北京,被一些朋友灌酒灌得半醉半醒,一群人跑到我旅馆房间起哄,要我帮忙算命。那天晚上不知道发了什么酒疯,我竟然答应了,帮忙一个接着一个算命,讲出的内容让当事人目瞪口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事情竟然被我准确地说了出来!这些朋友被这样的情况震撼住了,不但自己信服,还打电话给他们的朋友,趁我兴致高昂时,要他们也赶来旅馆向我请教。或许因为酒精的作用,我记不清楚当晚的事情,朋友事后告诉我,当天晚上我一连帮二三十人算命,每个人都惊讶不已,欲罢不能,直到半夜两点多,朋友们实在不忍心再打扰我,把大家赶出我房间,帮我抬到床上睡觉。
我把这件事告诉倪老师,老师一点也不惊讶地说,你现在知道到“师”和“匠”的差别了吧,“匠”是靠牢记条文去算命去看病,“师”是靠心灵感受去算命去看病,这中间的差别只能自己感受,无法用言语解释。
那件事之后,我的天纪功力似乎往上了一大层,也因此开始有些恃才傲物,帮人算命时常常会多说很多,给人许多的“指点”,自以为是帮助他人,其实只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没过多久,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蹦了出来,每次帮人算命后就会遇到一些麻烦,虽然没有让我实质上损失什么,却让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向倪老师请教,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你知道为什么“看病不算命、算命不看病”的道理了吧!我立即茅塞顿开,戒慎恐惧,保持谦虚。从此不直接帮人算命,即使人情压力下,我也只以人生阅历多一些的角度下,如同商业顾问一般,提供一些人生道理的咨询。
讲天纪时,又胖又壮实的倪师
2011年四月,我回台湾,到倪老师台北基隆路的家里问候老师。虽然老师依然侃侃而谈,看得出来神情上没有以往那股强劲的力道,老师缓缓地解释,他前一阵子身体不舒服,因此比较少和我在网上聊天。
师母趁老师不注意时,悄悄地告诉我,老师给自己开药后,都不好好服药,要我找机会劝劝老师,师母说大概只有我能劝得动老师。我很难过、很担心,我正准备要和老师谈这件事时,老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拿起电话打给台北汉唐诊所,要当时管理药房的尧钦制作一包十枣汤胶囊。老师挂上电话后,转头告诉我:“你常常到各地出差,北京上海冬天很冷,你得注意身体,晚一点你去诊所拿十枣汤胶囊,以后出差都带上,以备急需….”。这让我很感动,师母和我正在担心老师的健康,老师自己却想着帮我做好准备。
那次到台湾,我太太和年幼的儿子正好也在台北,即使倪老师显得有些疲惫,他坚持要带我们全家到阳明山上用餐及参观他新改建好的房子。老师要我先到台北诊所拿十枣汤胶囊,在那等他来接我们。老师亲自开车,老师说Nissan GT-R太嚣张,容易被警察抓超速,Volkswagen GTI Turbo虽然只有200多匹马力,因为车轻小,在台北市区开起来更灵活。师母坐在老师旁边,我们三个挤在后座,还没坐定,老师用力踩油门,冲了出去。老师把Volkswagen GTI Turbo当成Nissan GT-R来开,从台北市区一路飙上阳明山,老师开车的劲道,比我当年念台大时飙摩托车还更强大。
这也让我和太太想起来,当年我骑摩托车带她从罗斯福路、中山北路,一路飙上阳明山、金山,再飙回天母送她回家。感受到老师这股飙劲,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儿子还冒出一句:“爸爸老师好像比爸爸还会飙车!”
倪老师和师母找了一家隐藏在阳明山树林里的餐厅来款待我们全家,老师说这里的菜最好、最新鲜,我们也不客气地开始享受美好的餐点。餐点用尽,正当我们准备赶往老师阳明山新家时,老师开始有些喘。老师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掩饰,他拿出了小青龙加石膏汤科学中药粉剂,要我帮他倒杯温水来冲服。看到老师喝药的样子,我忍不住眼眶湿了,又不想扫大家的兴,悄悄地转头把眼泪擦干,结果还是被师母看到了,师母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眼神,似乎在提醒我多劝劝老师好好服药,我的心都揪在一起,我真的应该常回台湾探望老师!
用餐之后,我们来到倪老师阳明山的新家,老师兴致盎然地解释他怎么找到这块地、怎么把农舍改成豪宅、怎么装修他的个人音乐工作室等等,老师指着对面山头的一个农舍说,他本来打算买那块地,对方怎么都不肯降价,交涉胶着时,现在这块地正好上市求售,他顺着机缘改买了这块地来改建。
我们让倪老师在客厅休息,师母带着我们全家到广大的院子参观,整块地是往上爬坡的,我们一面往上,师母一面和我们闲聊他们从佛州搬回台北的过程,佛州诊所由“鸟蛋”接手经营(“鸟蛋”是李大叔Jack的外号),桃花岛上的住家还空着,偶而Jack会去帮忙打理一下。
参观过倪老师阳明山新家后,老师开车送我们全家回旅馆,在旅馆大厅前和老师挥手道别,那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倪老师。本来说好了十月要再回台湾看他,我因为加州的事情繁忙走不开,不得不取消了那次的亚洲行程,这也让我错失了再见到老师的机会。
杂乱地讲了几个我和倪老师互动的故事,和我跟随倪老师学习中医及老师要我负责传承他教学工作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么多年来,许多人告诉过我,他们梦到倪老师讲解中医或交待任务,就连师母也告诉过我,梦见倪老师要她把书拿给我,我却只梦见过倪老师和我吃喝玩乐。然而,许许多多和老师互动的故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也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讲人纪后期,倪师已经相当瘦削
倪老师正式退休搬回台湾前,我帮老师举办及主持了他一生中最大型的公开演讲,老师在飞来旧金山湾区前,寄了一封电邮给我,他说:“这次的演讲对经方未来的发展很重要,这次由我主讲,希望下次是由你担当此重任,你是老师最看好的一位。”在倪老师的厚爱及信任下,我开始在各地重要的医学研讨会中阐述倪老师的教学内容,从中国医药大学五十周年特邀主讲、连续几届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班、加拿大国际传统医学大会等,到这次新冠疫情大爆发下,中医抗疫成效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倪老师经方思维的卓越。当我每次在计算机前写文章、写医案时,都会想起当年半夜在网上和倪老师聊天的场景,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好像在跟倪老师报告我做的事情、治疗的病例,战战兢兢,却又有倪老师和我师生互动独特的风趣!
哲人已远,典范长存。倪老师永远是我这一生中最特殊、最有意义的老师!
李宗恩 谨记于加州辛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