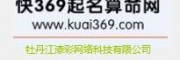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秦楚刊号
午属马。《诗经·小雅·吉日》有这样一句话:“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唐代孔颖达的解说是:“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就是说,选择午日为“既差我马”的吉日,只是由于十二生肖午属马的缘故。宋代王应麟将此举为“午马之证”。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庚午对马,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马为六畜之首。马的驯化家养,在六畜中却大约是最晚的。一般认为,将野马驯化为役畜,是父系社会时的事情,最早始于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人们已开始养马。许多古籍中有“相土作乘马”的记载。历来讲述上古史,以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作乘马就是发明用四匹马驾车。这反映了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商部落畜牧业的发达。后来,相土的后代打败夏桀建立了商朝。甲骨文中已有“厩”字。《管子》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养牲畜,“皂”是喂料的槽,“牢”是圈。
在漫长的岁月里,马不仅是拉车的畜力、代步的坐骑,其本身还是文化载体。有副春联,是供农历马年选用的:“骅骗开道,骥骥呈材。”八字联语中,“马”偏旁的字占了四个,语出《庄子·秋水》“琪骥骅骚,一日而千里”。汉字对于马类称谓区分之细,可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仅就马的毛色而言,職色黑,骊色黑,为浅黑,骥为青黑,驿色赤,驗色紫,骓黑白相间,暇赤白杂色,为黄白色;此外,黑白杂毛曰辆,黄白杂毛曰胚,青白杂毛曰聰,骠为黄色有白斑之马,驷为浅黑杂白之马,骗为黑鬣黑尾的红马……这些方块字,犹如五光十色的宝石,其间所凝结的,是古人对于马的观察、描画以至敷彩。这一切,反映出古人对马的偏爱,还体现了古时马在社会生活所占据的重要角色位置。美国汉学家爱伯哈德《中国符号词典——隐藏在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说:“马是中国人生肖中的第七种动物。在中国古代,有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马。这些词汇的死亡,表明马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此话有理。那些关于马的字和词,以丰富多彩的阵容,显示着古代马文化的博大。
票骗琪骊之类的“马字”,似乎又不只是马的“色标”,而马的精神风貌,古人在端详马字本身时,即已揣摩于心了,这便是许慎《说文》讲到的“马,怒也,武也”。一怒一武,刚健且道劲,凛凛威风,仰天长啸惊天,四蹄掠地无阻。还有那句“马到成功”,浅显而形象,体现了“快马加鞭未下鞍”的狂解突进,和“关山度若飞”的胜券稳操。杜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一往无前的气势,跃然纸上。相传西周穆王远游,出行时取八匹骏马,《穆天子传》记为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疆、绿耳。这一组马之名,透露着体貌与毛色的不凡。到《拾遗记》八骏分别作绝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从名称看,不仅骏马添翼成飞马,而且“超影”“超光”又“逾辉”,简直可望超光速了。
出类拔萃的马叫千里马。千里马的话题讲了几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枝奇葩。《战国策·燕策》载,郭隗向昭王论说人才问题,拿千里马打比方,讲述了千金求骏马、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返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马之至者三。”五百金买下死马之骨,以示渴求千里马的诚心。说买马,讲的是求贤纳贤。相传,燕昭王听郭隗之劝,在今河北易县筑黄金台,招揽贤能。
千里马成为美喻。汉武帝《下州郡求贤诏》,有“马或奔提而致千里”之语。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渴求“非常之功”,故求“非常之人”。只要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在乎他受到世俗的非议,只要是千里马,不在乎它蹶子。武帝曾以千里马称赞皇家后代,《汉书·楚元王传》: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千里驹即千里马,刘德年纪尚小,武帝因而这样夸赞他。
马与龙,传说中的一对双璧。明代小说《西游记》里,唐僧的坐骑白龙马本是一条龙。小说家的这一描写,便有着传统文化的、民间俗信的背景。
吴承恩构思这部神魔小说,人物多涉因缘。唐僧前世是如来佛的二徒,名唤金蝉子,因轻慢教义、不听说法被贬,转生东土,九九八十一难,取经以成正果。孙悟空大闹天宫闯了祸,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成了妖猴。猪八戒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蟠桃会上酗酒戏仙娥,被贬下界投胎,身入畜类。沙和尚原为玉帝跟前的卷帘大将,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被贬下界。他们都是观音菩萨相中的人选,在取经西行的路上候着,等待做唐僧的徒弟。取经功成,五圣成真。这五圣,除了唐僧师徒四人,还有白龙马——他成了八部天龙马。
《西游记》讲,白龙马原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子,称玉龙三太子。他纵火烧了龙宫的明珠,龙王向玉帝告他许逆。这是死罪,观音菩萨求情,讨他下界,在蛇盘山鹰愁涧中栖身,等唐僧来时化为马,充当取经人的脚力。书中描写龙变马的一幕: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随即变做一匹白马。白龙且白马,因为他出自西海龙宫。依五行之说,西方色白。龙分五色,西海潜白龙。
《西游记》是中华传统文化沃土培育的奇葩。它的人物设置、情节构思,往往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白龙马即是如此。小说第十五回描写,孙悟空对这条“有罪的孽龙”并不认可,观音菩萨开导说:“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这万水千山?怎到得那灵山佛地?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小说第一百回,如来佛为五圣封号,说到白龙马:“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这些话语,如同一个模子扣出,那模子就是中国古老的传说:龙马河图。
龙马河图,是关于中华文化发韧开端的神话。相传,伏羲之时,黄河出现龙马——龙头马身的神兽,马背旋毛如星,组成一幅图,称为河图。伏羲心有灵犀,按照河图上的自然数,创造了八卦。《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出图,即指龙马河图的传说。
《西游记》的白龙马,显然是龙马的翻版。西天如来要将真经颁于东土,前去取经者各有来历,均非凡人。而那经卷,必须由白龙马去驮,方显经之真、卷之珍。
当然,吴承恩创造白龙马这一角色,大约也借鉴了白马驮经的佛教佳话。据史载,汉明帝曾有金佛之梦,由此造使西域,迎进佛教。这是中外文化一次历史性的交流,汉使、梵僧,会合于大月氏国。一方西去寻梦,一方东来宣教,会合后便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东汉国都洛阳。转年,洛阳修建中国第一佛刹,命名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这白马经,与龙马出河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龙马要高八尺五寸,不是随意标出的尺寸。《周礼·夏官》:“马八尺以上为龙。”《说文解字》也采用此说此解。尺寸多么大并不紧要,重要的是设计了量变与质变——马和龙之间画一条界线。有了这条线,在人们驰骋想象的天地里,要越线过界,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汉武帝得良马,为庆贺此事而创作《太一之歌》,歌中唱“今安匹兮龙为友”,反映了古人的龙马观念。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个马师皇,相传为黄帝时的马医,汉代刘向《列仙传》说他“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精于医马的马师皇,还能为龙治病。一次,有龙前来,马师皇说:“此龙有病,知我能治。”于是扎针、灌药汤,治好了病。从此,常有病龙从水里出来,请马师皇诊治。再后来,有一条龙索性驮走了马师皇。明代刊刻《列仙全传》中的马师皇,被刻画为正在给飞龙扎针的图景,身旁卧着马。马师皇传说的文化底蕴,在于反映了古人心目中龙马归一观念。
马化为龙,唐代柳宗元《龙马图赞》说,唐玄宗时,得异马于黄河,有人画下马的样子,“龙鳞、他尾、拳髦、环目、肉鬣”。此马在御厩中饲养近二十年,曾随玄宗封禅泰山。安史之乱,玄宗西逃入蜀,“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去”。不愿再陪伴落难的天子,陆上马变做了游水的龙。
马的典型风格,是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它的不受羁绊,它一日千里的狂奔,用一个常用词表示之,就是“烈马”。由马而及火的联想,既生发于驰马剽悍的阳刚形象,也得益于“午”对马形象的归纳和提升。这提升,将马之烈,挂靠于宇宙乾坤的哲学框架之中。请读《元享疗马牛驼经》:
混沌初分,天地始辟,午丑之象,各从天地而生。午者阳火也,应乾象而生马;丑者阴土也,应坤象而生牛……
马和牛相比,在动物习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古人解说这种差异,将其置于天地开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午丑之象,各从天地而生”。午马为阳火之象,丑牛为阴土之象,从而注定马与牛不同的习性特征。
下期继续请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