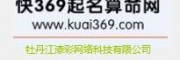左起:冀淑英、顾廷龙、潘景郑、沈燮元。(作者提供/图)
上海图书馆三老——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尽管沈津先生都写过纪念文章,但相较而言,瞿凤起先生身后却最寂寞,想必没有人提出异议。犹记2019年6月30日《南方周末》曾刊登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回忆与瞿凤起先生交往的片段,题为《寂寞的铁琴铜剑楼——记藏书家瞿凤起先生的晚年》,标题恰好用的就是“寂寞”二字,文中一些细节,时隔多年,读之仍令人动容。2023年4月中旬,我曾向南京大学历史系胡正宁先生探询谢先生的近况,因他与沈燮元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在沈先生遗留下的信件中,已故者数量较多的是顾廷龙、冀淑英、王绍曾等几位前辈,健在者较多的几位里,谢正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谢先生已年过八旬,但以二人的交情,听闻沈先生逝世,他肯定要写一点纪念文字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胡正宁先生处听闻谢正光先生罹患疾病,无法再亲笔砚的消息,不免让人慨叹。
一回头看追忆瞿凤起先生的文章中,无论是沈津先生,还是谢正光先生,都将瞿凤起先生的生年写作1907年,其实是个小错误。瞿老的同乡、常熟曹培根先生《铁琴铜剑楼研究》中《瞿凤起生平事迹》一节,记其“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十八(即公元1908年6月16日),1987年3月1日逝世,享年80岁”,显然更为准确。虽然我没有看到瞿氏家谱或瞿老个人档案,但可以确定瞿老生于1908年,为何如此肯定,实源于他常用的一枚闲章——“惟戊申我以降”,与文徵明的“惟庚寅吾以降”(取《离骚》成句入印)相近,纪其生也。戊申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是瞿老出生年份最好的旁证。
沈燮元先生藏有一部《二金蝶堂印存》,书前有吴湖帆题耑,顾廷龙、潘景郑二老题诗词,顾老题诗已收入《顾廷龙文集》。书后有瞿老跋,未曾刊布过,跋文所用引首章即“惟戊申我以降”朱文长方印(下图)。其文云:
此《二金蝶堂印存》二册,闻系吾邑篆刻名手赵古泥家散佚者。吾友沈燮元先生所得,属为记言。偶读潘氏《还砚堂金石书画题跋记》,于赵氏印谱一则有言曰:“朱文似完白一派,白文则直造汉人堂奥,而款识之精绝,宛似一幅缩临郑文公碑,一技之精,进乎大道。”云云,余不谙六书,无可言。因假潘氏之言录而归之。壬戌九秋,常熟后学瞿凤起。
《还砚堂金石书画题跋》是苏州“贵潘”后人潘志万的著作,只有手稿传世,并未刊刻,原本旧藏顾氏过云楼,今在南京图书馆。抗战时期,瞿凤起先生与顾家后人顾公雄、顾公硕两兄弟同居上海,交往频密,顾氏兄弟刊刻乃翁顾鹤逸《鹤庐画赘•鹤庐题画诗》,刻工就是瞿老所介绍。尽管彼时过云楼藏书之名,无法与铁琴铜剑楼相媲美,不过瞿凤起先生仍不时借抄顾氏藏书。沈燮元先生《顾氏过云楼藏书之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列举过云楼藏书归公藏之前八十年间,经眼顾氏藏书的九人里,第六人便是瞿凤起。上海图书馆藏有瞿凤起先生手抄《鹤庐藏书志残稿》一种,原稿长期保存在顾笃璜先生处,前几年方才捐存苏州市档案馆。记得潘氏《还砚堂金石书画题跋》一种,稿本之外,还有一个抄本藏于常熟图书馆,就是出自瞿凤起先生的捐赠,极有可能也是瞿老手抄,所以他在为沈燮元先生题《二金蝶堂印存》时,应该特意找出昔日抄录的册子重温了一下。关于这个推断,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机会去常熟亲眼看一下此书,便知对否!
二今夏整理沈燮元所留什物,于遗箧中陆续检得瞿凤起先生书札数通,时间介于1981—1986年之间。其中,1982年11月5日一札提到为《印存》作跋一事:
燮元先生史席:潘景郑兄交陈光贻兄带下尊藏《二金蝶堂印存》二册,嘱为一言,勉假潘文书之,聊以塞责,不足附列也。原书仍存上图潘处,俟台从来沪,由其面陈。拙稿附上。
由此可见,《二金蝶堂印存》后的瞿老跋文作于1982年10底或11月初。此前一年,沈燮元先生致函瞿老,询问其祖先、铁琴铜剑楼历代主人生卒年,为此两人于1981年函札往返数次,1981年10月7日瞿老覆函:
燮元先生史席:别久为念,顷由潘景郑先生转来九月廿三日惠示,奉悉。承询先高祖考生卒年,谨按:先高祖生乾隆三十七年,卒道光十六年。先曾祖生乾隆五十九年,卒道光二十六年。先伯祖生嘉庆二十五年,卒光绪十二年。先祖生道光八年,卒光绪三年。先父生同治十二年,卒民国廿八年十二月(一九四〇年一月),张鸿志铭。关于藏书事迹,有邑人顾君一文,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光明日报》,以及五渠族人瞿冕良撰《漫话铁琴铜剑楼》载常熟政协编印之《文史资料辑存》第八期(最近出版),可资参考。
(作者提供/图)
沈先生得信后,将以上瞿氏四代人生卒信息开列成清单(上图),再寄上海请瞿凤起注出其先人的名字。同年10月12日,瞿老又说:
燮元先生史席:前函所询先世历代生卒年,系依来示所列名单为次,故名从略。顷又奉十日手示,知未解此意,缘遵嘱填入,随函附还。
名单中硬笔系沈先生所写,毛笔小字填入,系瞿老手笔。沈先生之所以向师友询问生卒年资料,可能是帮同事宛雨生先生咨询的。昔年沈先生告诉我,宛雨生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宛敏灏的侄子,是他一起在南图古籍部工作的同事,长期从事清人生卒年资料的搜集工作,编有《清代历史人物生卒录》稿本一种,收录清人一万余家,凡十余册,可惜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出版。记得我在南京读书时,沈先生每逢周末常去龙蟠里看望宛先生,据说宛先生晚年只有一位保姆照顾起居,十分孤单。这一点,与暮年的瞿凤起先生很像。我离开南京几年后,有一次沈先生告诉我,宛雨生先生去世了,并说家里的稿子也流散无遗,谈及《清代历史人物生卒录》没能出版,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不禁让人想起古人诗中“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之句,若忽略时空的差异,人与人的关系与情感,有时并无二致。
瞿凤起先生。(作者提供/图)
三晚年的瞿凤起先生,正像谢正光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与寂寞相伴,对主动上门拜访的朋友总是存着期盼。1986年他写给沈燮元先生的几通信,基本上都是约沈先生去他家晤谈,如1月23日言:
燮元吾兄大鉴:不聆教言,倏又多日,怀念之至。返苏之日,想不在远,因有件托带,拜恳行前过我,俾便交付,无任翘盼。
沈先生得信后,应该不久便去了北京西路1290号瞿家。1月31日瞿老又写信道:
昨匆促间话别,回思尚有未及者:(一)会见夏或瞿两公时,告以弟有宋刊明印残本《宋书》及陈鳣、张燕昌(兔床上款)尺牍数通,又张廷济诗笺一页,如馆能收购,便乞过我面洽。(二)苏城文具店如有卷铅笔之刀,乞代购一枚。弟近需商务《续古逸丛书》全目,奉烦就《丛书总录》复印一份,就便交下,俾资参考。琐琐渎神,容当泥首。
信中的夏应是夏淡人,民国间在江氏文学山房学徒,后独立开设琴川书店,公私合营后,转入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瞿为《漫话铁琴铜剑楼》一文的作者瞿冕良,当时与夏氏同供职于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有《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据谢正光先生《寂寞的铁琴铜剑楼——记藏书家瞿凤起先生的晚年》所述,瞿凤起先生居住的“亭子间里仍堆着一包包用旧报纸包好的书。桌上、杌上、床头、床底下都有,而且堆得也颇为整齐。包外没有标记,别人是不知道他有些什么书的”。听沈燮元先生回忆,瞿老曾借他一部册页,整个全是清人蒋因培的手札,应该就是旧报纸包的书中的一种。这套手札放沈先生处很长一段时间,在他还给瞿老之后不久,就传来瞿凤起先生过世的消息。沈先生对我感叹道,幸亏归还及时,不然就真对不起老先生了!
瞿凤起先生的著作并不多,较常见的有《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与潘景郑先生合作校订的《千顷堂书目》,还有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先人所遗《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此外单篇文章寥寥无几,以至于到今天仍无法编集成书。从1984年9月26日致沈燮元先生信有“顷出版社送来《题跋集录》二次校样,乞将前假稿本于返苏度假前掷还,俾便及时完成任务”之语,可见当时瞿老曾将《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底稿借给沈先生。1985年1月8日信又说“岁尽暨一月六两休沐日,恭候驾临,未见下顾,知《集跋》尚未校毕,然否”,听起口气,似乎沈先生也曾帮着校对稿件。
还有一事不能不提,那就是瞿凤起先生也素有整理黄丕烈著作的志愿,在1981年12月11日他写给沈先生的信中便曾说:
燮元先生史席:五日惠示奉悉,拟辑黄丕烈逸文,缪辑跋文后出者,欣夫已有《续跋》及《再续跋》刊本,渠复辑黄诗,尝从录副,今已无存。其中有《题红豆花四绝句》,为吾家旧藏,特抄录随附。承赐《永丰乡人行年录》,拜领,谢谢!
又,次年7月21日一札说“顷理书夹,获荛圃跋录文(二则),亟检出,适朱荣琴驾到,奉托转呈。如已入录,便乞掷还”。沈燮元先生曾以瞿老朱笔过录批注本《荛圃藏书题识》见示,眉端蝇头小楷,密行细字,在在有之。记得北京韦力先生也有一部墨笔批注本(《芷兰斋书跋四集》著录一种,题为张乃熊批校),沈先生曾让我向韦力先生求得有眉批的那部分书影,粗粗校对之下,发现朱批本内容竟然还略多于墨批本。从内容看,应该是瞿老在前人基础上,将自己所见所闻加于其上。巧合得很,此书卷端也钤有“惟戊申我以降”一印。
《红豆华图册》中毕琛摹绘柳如是儒服小像。(作者提供/图)
四最后,须补充说明一下,瞿老致沈燮元先生信中所附带抄录“为吾家旧藏”的《题红豆花四绝句》,原册现藏常熟博物馆,册前有石韫玉题“春生南国”四字引首,画共三开,分别为毕琛摹绘柳如是儒服小像、杨旭画折枝红豆花图、瞿麐画红豆村庄图,杨、瞿两家所题上款均为“荫堂”——瞿绍基,册后有清人孙原湘、黄丕烈、尤兴诗、彭希郑、张吉安、言朝标、蒋因培七家及近代张双南、瞿凤起二家题跋。瞿老跋作于1950年,据其自述,此前他便有辑录黄丕烈诗文之志:
此为吾家旧物,幼时未曾见过。曩余辑黄氏诗文时,先君尝告余《红豆华图册》中有题诗,曾经录出。但原册为张双南借去,向其追索,云已归还。越三十余年,在里中有人持此册求售,云从张氏之女某家散出。因系吾家旧物,请备价收回。余告以曾为张氏借失,但无物证,只得备价收回,因记其颠末如右。
此时,距父亲瞿良士去世已经十年之久,瞿凤起先生的跋写得依然十分克制。与前面被保留下来的1943年8月张双南跋语谎称“辛亥乱后,不知如何散出,余以重价得自冷摊”同观,两家之高下自可立判。据沈燮元先生告知,瞿老所辑录的黄丕烈诗文集他曾借阅过,归还瞿家后,不知是否已被瞿老与藏书一同捐回了故乡常熟。
李军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