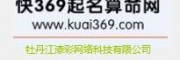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原作者:旷野孤行客。摘自《个人耳闻,可信度很高的鬼故事》)
我们这地方,大概是和湖南差不多,古时巫蛊之风比较兴盛。不管是传说也好,附会也好,反正有奇能异术的人比较多。
在我们这,“看相”、“算命”、“拣日子(挑个吉利的日子)”算不上有多神奇的学问,但凡和宗教、巫术、“邪教”沾点边的人,大多会一点。
各派方法不一,各有所长。我们常说“文人相轻”,其实,我们那,有点“道艺”的人,也往往彼此不服气。只不过,能学到“道艺”的人,性格往往比较内敛,对于门派之争,多是在熟人前评议几句,或者冷冷嘲讽几声。所谓“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不会有太大的纷争。
唯独在“看相”方面,大家都服一个人,没人敢自称超过他。
这人姓章,大家都称他为“章公”。在我们这,“公”这一称呼,是对长者的尊称——一般来讲,对年龄很大,不知道如何按照辈分来叫的,都称公了。
章公长寿,我祖父年轻时,称他为“公”,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叫他“章公”。
章这姓,在我们那一小片地方,就一支,人丁向来不旺。虽然属于杂姓,但章公家在我们那很受人尊敬,因为他家代代出“打师(武艺高超的人)”。以前的打师,都要懂经络、穴位和关节的学问,因而一般都精于治疗跌打损伤之类的病。
章家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就立了规矩:出门在外,看到有人受伤(扭伤、摔伤之类的),必定要救,最少要治到让受伤的人走回家;在家,人家求上门来了,能治一定要治好。在外救人,不能收钱,不过,要是人家找上门来“填谢”(感谢),不管多少东西,收一半。在本乡本土,帮人治病,可以吃饭,不能收报酬。
章公的父亲,是一位“大佬打师”(技艺高超,数一数二),在我们那打出了名声。章公父亲的武功,属于“倒山”一派。
“倒山”这功夫,顾名思义,出手如山倒,没人抗得住。据说,“倒山”其实属于“邪教”,因为它完全违背了物理理论。太极的四两拨千斤,是借力打力,而“倒山”,不需要借力,完全是凭空发力,瞬间击倒对方。
“倒山”又分“上倒山”和“下倒山”。“上倒山”一出,对手必定倒地,多是受外伤;“下倒山”一出,是要“进脏腑”的,专取人性命。
“下倒山”在我们那算是最狠毒的武功了,因为前面我讲到过的“五百钱”的点穴功夫,只要出手的人愿意,大多还是有办法挽救的,“下倒山”一出,挨着的人当场就会重伤,没有办法挽救,只能等死。
章公这人,用我们那的话来说,是一个“嗷嗷叫”的人,“嗷嗷叫”是脾气比较直,但心地善良办事公正的意思。
在我们这有句俗语:交人(和人交往做朋友)宁交“嗷嗷叫”,不交“嘻嘻笑”。
章公生得不是很高大,但“横把很扎实”(强壮)。他父亲是“大佬打师”,但性格很平和,能忍的事总是尽量忍,生怕多得罪一个人。
章公性格却完全相反,眼里完全容不下沙子,从不肯低半分头。
有一次,我们那里有几个人到临县的山里挖冬笋,被当地人收了锄头和柴刀——本来,挖冬笋对竹林没有任何伤害,反而有利于春笋生长。临县的人也是仗着本地人,故意欺负一下我们那人的。
章公那次没去,也只是听人说了,也不和人打招呼,连夜冲到临县收我们那人锄头和刀的人的家里,一脚踹开大门,吼道:“你们不是要充屋檐霸王么?今我就来试一下!”
临县那户人家,有五六兄弟,也都是练过的,但慑于章公父亲的威名,只能忍气吞声,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还有一次,是我们那“当闹”(赶集)。赶集各个镇(以前叫什么不清楚)不同,有些地方是三天一闹,有些地方是十天三闹。我们那,一年就一次,因而比较隆重。
我们那有个人,家里很穷,性格比较懦弱。在一个油条摊前,本想买根油条,手拿了一根,然后一问价钱,才发现自己买不起,于是又放了回去。
卖油条的老板,是个外县人,欺负我们那人老实懦弱,就讽刺说:“你快走远点,一个老表样还吃得起油条!”“老表”这词,多形容一个人穷、打扮落伍,有极大的羞辱的意思。
我们那人一下子羞得面红耳赤,眼睛都红了。乡下人,平时谨小慎微,为的就是保留做人最后的一丝尊严。现在为了一根油条被人耻笑,勾起了这个穷苦人的悲伤,但人穷志短,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讪讪地离开。
这时,章公正好也走到了油条摊前,一看我们那人很伤心,一问,不禁怒气冲天,拉了我们那人,走到油条摊前,问摊主:“你这是卖什么的?”
摊主一看章公这块头和气势,有点怕了,连忙说:“卖油条哟!”
章公拿起油条摊上的一个锅铲,在桌子上重重一敲,说:“我还以为你这是卖金条哦,卖几根油条就这么拗(嚣张的意思)?”说完,也不说话了,拉了我们那人,就站在油条摊前,有人来买油条,他就一挥手:“今这油条不卖了!”
油条摊老板一看阵势不对,连忙去叫同乡(一起赶集做生意的)来帮忙,其中一个远远看到章公,连忙对油条摊老板说:“这个人我们惹不得,他爷老子就是某某呀,出了名的大佬打师,今要是动了手,我们还回得去?”
油条摊老板一下子没脾气,只能上前对章公说:“老弟,今是我错了,我也是走了这么远,生意又不好,心里不好过,事(话)说错了!”
然后又对着我们那人笑着说:“老弟,我早上是多吃了两口酒,脑壳昏了,你莫见怪,来,吃!吃!油条尽量吃!”
章公抓了几根油条,扔了一把钱,说:“你跑这么远来赚几个钱,我也不是讹你,你不改,下次等(让)我晓得,摊子都要掀掉你的!”说完,便拉了我们那人走了。
章公的行事,就是这样。以前学武的人,第一讲究忍,章公这样的性格,他父亲不敢传真功夫给他,怕他惹事,只教他一些“硬柴功夫”——强身健体,让身体变得灵活和增强抗击打能力的功夫。
章公的爱打抱不平,是天性使然,并不是他武功有多厉害。
后来章公结婚生子了,脾气慢慢有些收敛了,他父亲才敢慢慢传授一些真功夫给他。世间的事情,都逃不过一个“好(喜欢)”,章公家族可能有这样的基因,章公对练武很是痴迷。以前农村人自由支配的世间较多,章公因而练得不错,慢慢的,在我们那也打(比武)出来了一些名声。
一年冬天,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章公问他父亲:“爷老子,你说你后生时候,跟我来搞,哪个搞得赢?”
章公父亲这时六十多了,平时身体不是很好,听了儿子的话,笑了笑,说:“你这几下硬柴功夫,还要我后生?而今我要把你搞成怎么样就搞成怎么样!”
章公这人豪爽,他父亲也不古板,因而父子关系融洽。章公笑着对他父亲说:“爷老子,莫好高(吹牛),而今屋里那棺材都呀呀作响(按我们那说法,晚上棺材发出声音,预示着棺材的主人要死了,此处是玩笑话),要装你了,你还搞得我赢?”
父亲也不生气,说:“不是我说,我哪怕是瘫在床上,只要没落气(断气),搞你都只要一下!”
这时,章公老婆插话了:“爷老子,你们今就试一下呀!”儿媳妇进门,只听说公公是“大佬打师”,没见他出过手,因而很好奇。
章公父亲这晚兴致很高,说了句:“来就来!”
一家人于是到了大厅,父亲对章公说:“儿呀!你看,今我要你倒到三个地方!”说完,用手指了大门边,说:“第一下你倒到(在)这”,又指着八仙桌下说:“第二下,你倒到这”然后指着门外说:“第三下,要请你出门!”
章公自然不服气,对着父亲说:“您老人家几十岁了,今莫被我打得哭,说我不孝哟!”
章公这时也三十多了,留了一个心眼——败给自己父亲不丢脸,但不能他要我摔哪就摔哪。因而第一次站在离门边很远的地方,用我们那话来说,是“站好桩”。
父亲也没提异议,对章公说了句:“按说,打架要让别人先进桩(按我们那说法,两人对打,谁先动手谁吃亏),今我来进你的桩!”
说完,一个箭步,迎面就是一拳,章公怕伤了父亲,不敢硬接,一个转身,准备绕到父亲身后,谁知父亲忽然“呔”一声,然后他就脑门一热,“扑”的一下,直接倒在了门边,直摔得眼冒金星。
父亲一拍手:“儿呀,你蛮听话呀!怎么我还没出手你就自己倒到门边去了?”
章公摔得有点懵了,不服气,对父亲说:“刚我是怕打断你的老骨头,我不让你,你会先睡翻(倒地)的!”
父亲摇了摇头,说“照你这样说,是让了我?这样,这次你来进我的桩,你倒桌下去!”
章公吃了次亏,变得谨慎起来,出手前,下架(马步)注意了,免得被掀翻,谁知道,还没近身,他父亲大叫一声:“下去!”章公一阵眩晕,等回过神来,父亲已经笑嘻嘻伸手来拉他。
章公这时已经服了,但仍不相信父亲有这么厉害,一用劲,对父亲说:“爷老子,你也到桌子底下来坐一会!”章公刚准备拉他父亲下来,又只觉得整个人忽然间空了,在大厅里滚了几下,直接摔倒门外去了。
章公老婆连忙去扶,章公父亲笑着说:“他皮厚,不要紧!儿呀,你爷老子没好高吧?”
章公一下子心服口服了,连忙缠着父亲问究竟,父亲笑了笑:“当师傅,不留两手,不会被徒弟打了啊!时候还没到,等我快死了再说!”
过了两年,一个晚上,鸡叫一遍的时候(大约晚上三点的样子),章公父亲要章公到他房间去。
一进门,看到父亲房里桌子上,香案已经摆好,香呀烛呀之类的都点起来了,父亲说:“某某,今我就教你点真道艺哦!来,跪下!”
说完,父子俩都在香案前拜了三拜,父亲起身,坐在桌子旁的凳子上,说:“拜我三拜!”
章公拜完,父亲拉起他说:“对着香案,赌个誓愿(毒咒),今学的东西,要是乱用,会怎么样?”
章公耳濡目染,自然知道,发誓说:“要是乱用,我不得好死!”
章公父亲才列明什么时候可以用“倒山”功夫,问章公:“记得么?念一遍!”
章公念完,章公父亲才把这法术的口诀传授给他,并要章公在他自己身上“试手”,摔了三次后,告诫章公说:“儿呀!这东西,损生,不是狭路相逢,人家要收你的命的时候,千万莫用!”
又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章公躺在床上,只听见厨房方向,有锯窗子的声音(偷腊肉的)。他心里纳闷:“有这么瞎眼的贼?”,于是在床上咳了两声,意思是告诉盗贼,我已经听到了。
章公父子都是打出名的人,有自信没有人敢动他家的东西。谁知道,半个钟头的光景,锯窗子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章公暴怒:有这么该死的贼?于是悄悄出了房门,盗贼可能听到声音,连忙逃跑。
章公哪里肯罢休,追了一阵,终于看到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射(用力踢)”一脚,谁知道盗贼也练过,往旁边一闪,章公踢了空,人还没收住,对方一转身,朝着章公头上一拳,力道很大,打得章公一下没了方向。
盗贼打完,又连忙逃跑,章公受了一拳,心里非常生气,拼命追了上去,左手抓了盗贼的衣领,猛的往后一拉,右手早抡紧了拳头,狠狠砸向盗贼的头,盗贼好像有了准备,章公的拳头还没到,他的拳头先到了章公肋下。
章公一惊,这人道艺蛮好,一急之下,“呔”一声,下出了“倒山”,用的是下部,准备收盗贼的命。
谁知道,盗贼一点反应没有。章公这下怕了,难道这人受得住“倒山”?
正迟疑时,盗贼回头笑了:“你这假倒山打得到人?”
章公一听声音,是自己的父亲,忙问:“怎么回事?”
父亲叹了口气:“唉!我这点没用的道艺,要失传了!”
然后拉着章公的手说:“儿呀,要是我是贼,我已经在跑(逃),对你又没害,你追不到就算了,硬要讲蛮劲!你这样,学了这东西,终究要惹祸,不要学了!”
原来,章公父亲故意要试试章公,那天晚上教的是假的。章公这人性格还是太好胜了,这样的人,是不能传“倒山”这功夫(法术)的。
不过,我们那的道艺,这一辈没法传,还有办法传到下一辈,就是先传给外姓,传的时候,要徒弟立下誓愿,有生之年一定要传回给自己的一个后代。
于是,章公的父亲,把“倒山”传给了一个姓王的徒弟。
章公有两个儿子,谁知道,脾气品性和章公一样,也不适合练武。
王姓徒弟年纪很大了,没有带徒弟,生怕这道艺失传,几次三番要章公允许儿子学“倒山”,章公就是不松口。
王姓徒弟没办法,就对章公说:“你这样,我就对不起我师父了,这样吧,我就把我祖传的麻衣相术传给你,也能混口饭吃,算我还师父的人情!”
章公所学的麻衣相术,和现在书店卖的“麻衣相书”应该没什么关系,具体是哪个流派,我就不清楚了。
据说,在此强调据说,章公的相术,属于下部,看尽天下的人。共分为九部:富、贵、贫、贱、忠、奸、善、恶,外加一部“常人”。
为什么叫下部呢?相传是阎王爷放了多少人到人间,这书上就有多少面相。但看不了“大龙大凤”——皇帝皇后(存疑)?看不了豪富豪贵的人。这些人不是从阴曹地府投胎而来,而是上天神仙罗汉下凡,所以书中不列。
阴曹地府在下,因而称下部了。
章公年轻的时候,从不给人看相,到了晚年,人生寂寞,才慢慢给周围的人看,也不收钱收礼物,完全是消遣打发时日。因而,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才有了大名声。
按章公的说法,他在我们那小地方给人看相,极少用到前八部。都是“常人”的相,命运差不多,只是婚姻早晚、寿命长短、一生总体顺不顺遂的问题。整个我们那一块地方,也就十几张脸的样子。
算命讲“生有时,死有日”,阎王一放人,生死簿上标得分明。看相讲相貌,阎王爷放人,都是带了印记的(以后好收回)。这些印记,决定一生的走向,即便有些双胞胎,看似一样,实际仔细去看,仍是大不相同。
我们这,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大龙大脉,难有翻江倒海的人物,所以,看起来很简单,仔细看看阎王爷烙的印记,一生命运,基本八九不离十。
章公看相,看得不多,但都极准,丝毫不差,从没失过手。
一次,他从县城回家,路上,遇到我们那一个出嫁女子的丈夫,路途寂寞,两人就慢慢聊起来。
聊了很久,章公看这个男人神情有异,就问:“后生,我看你心里有事啊,今到做什么哟?”
男子支支吾吾,良久,才叹了口气:“说来跌鼓(丢人),今把我那个小的送到人家屋里了!”
章公一惊,问:“哪个呀?你老婆去年抱回娘屋(娘家)的?”
男子又叹了口气:“是呀!”
章公一拍大腿,说:“唉呀!有人穷不久呀,屋里只要还有口番薯吃,怎么忍得下这心!”
男子一脸羞愧,犹豫着说:“章公,你也晓得,我这个人,没什么用,而今四个伢(儿子),真是过不下!这个小的,你也晓得,都快三岁了,还是一个软麻糍一样,站都站不稳,又不晓得说话。这样的伢,要是生在有钱的人家,娘爷(父母)还伴得了几年,生到我这样的人家,日后饭都没得吃,也是造孽。”
章公摇了摇头,说:“后生,我这个人呀,就是好(喜欢)管点闲事,今我就多两句嘴,你也别生我的气,你屋里而今伢里(男孩)是有几个,论有靠,还是这个小的长久哦!”
男子只能苦笑:“章公,只要有一点点办法,哪个舍得做这样的事?也只怪这伢没福气,投(投胎)到我这样的屋里。”
章公笑笑说:“什么福气不福气,你要是把这小的送掉了,那真是没福气。你眼光真是蛮好,把支好灵芝去送人,自己留几块木耳!”
男子有点惊奇,说:“章公,你说这小的还是有福气的人?”
章公笑笑,说:“我们这一路(一带),还没有比这个更出众的!”
男子以为章公安慰他,也不答话,章公又说:“你这个小的,你听我讲,他而今看起来没什么用,他是越长越灵气,到时你看,他不会像娘,也不会像爷(父亲),我们这没有比他长得斯气(英俊)的!”
男子心情低落,也没多大兴趣和人“胡扯”,冷冷说了句:“人家都说三岁看老,他只要有中等的样子,我也不舍得啊!”
章公也不生气,继续说:“后生,这样,你告诉我你给了哪家人家,我去要回来,算我的孙,做得么?”
男子看章公不像开玩笑,就又问:“章公,你看他还真能长成个人?”
章公也不答话,用“三角班”里的调子哼了起来:“唉!都是命,我是求这样的人求不到,人家啊,有了又不珍贵(形容词意动用法,呵呵~~)!”
男子心中疑惑,问:“章公,我那个你哪看过?”
章公说:“去年你老婆抱回来,我一看,心里还惊了一下,我们这小地方,出这么一个人物,不容易,他这个人,一世都有贵人帮扶,吃穿就不说,你看得到,这伢,三十五岁后,顺风顺水,六十后,出门都有人抬轿哦!”
男子将信将疑,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经章公一说,心中不忍了。他这个人“没口语(不善于言辞)”,就对章公说:“章公,这就还要麻烦你去帮我要回来哦!”
两人走到天黑才到送人的那户人家,还差一里多的时候,就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男子一进门,平时不会走路的孩子,竟然挣脱了那家大人怀抱,直接跑到了他脚边,开口就叫爸爸,男子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那户人家,看父子哭得伤心,也没怎么挽留,让章公他们把孩子领回家。
路上,男子对章公说:“也真是奇怪,今他还又开声又走(开始说话、走路)。”
章公长舒一口气:“没什么奇怪,他就这相貌:不逢贵人不开声,开声声出金满厅;不逢贵人不开走,开走走出银千斗”。
这孩子到家,果然如章公所说,越长越秀气。当初他父亲把他送给别人,谎称他只有一岁半——个子太小,说三岁怕人家不要。只过两年多,就长得有七八岁孩子那般高了,更奇的是,以前农村的孩子,都是满世界跑,成天风吹雨淋,多是浑身乌黑,只有他,晒不黑,白白净净,我们那人给他取了个外号“黄牙笋”——没有出土的竹笋,黄灿灿的,形容男子貌美。
这孩子,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更加与众不同:一米八几的个子,面若桃花,我们那女子肤色没有一个有他好看;没读什么书,就在一个本家“借着(不是正式读书)”学了三四年,但举止文质彬彬,即便下田回家,也必定洗得干干净净。往哪一站,都是鹤立鸡群,有两家求亲的,为了他,不惜放下脸皮打架。为此,很多人打趣他父亲说:“你这是从哪借来的种?”
这孩子十九岁那一年,水稻“含苞(结穗)”时候,我们那不知道从哪飞出不计其数的蚱蜢。铺天盖地的,往哪一停,用不上半上午,就啃得“像用镰刀割了一样”,基本没有收获的希望。我们那的人,从来没听说过蝗灾,连“讲传”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人们都说:“这是要变天了。”
以前农村,都靠几块田地过日子,蝗虫一过,大部分人顿时没了依靠。年轻人聚在一块,商量来商量去,只有去“当兵吃粮”这条路了。
正好,我们那附近正“过兵(部队开拔经过)”。大家决定,去“拦马”。因为老人“讲传(历史故事)”,当官的都骑高头大马。
那次我们那“过兵”,过了四天四夜,第一天,大家站在路旁,犹豫着不敢去。第二天,又犹豫着不敢去。第三天,这些人一发狠心:死了就算了!几个人看准一个骑大白马的,手拉手往路上一拦,高喊要去当兵。
谁知道,这部队是从外地开过来的,听不懂我们那土话,那骑白马的,是一个师长,杀气很重,一看有人拦路,把腰间手枪一拔,还没举起来,我们那人就吓得“起掀的跑(没命逃跑)”,只有这孩子,昂头挺胸,一动不动。
这师长一看这小地方还有这么“英赞(英俊)”的人物,心里很喜欢,就停下马,在部队找我们这边人来当翻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伙夫,是我们邻市的,语言有点相像,连比带划,才弄明白意思。
师长把手里马鞭往这孩子手上一塞:“跑得了一里路就带你走!(当然是翻译了)”
这孩子二话没说,一跳上马,也不知道蹬马镫,两腿一夹,用打牛的力气,往马屁股上一抽。师长的战马,都是好马呀,这一鞭,马一下子跑了十几里路(他不会叫停,我们那没养过马,都是“讲传”里经常说,前面的兵认识是师长的马,拉了下来)。
这孩子到了军队(国民党部队),被师长送去学测绘。以前部队搞测绘的,都是人才,但孩子很快脱颖而出。一个是他是师长送过来的人;二个是他农村出去的,吃得了苦,交代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偷懒敷衍;三个是他记忆力惊人,到一个陌生地方,哪怕是骑马跑过,回去以后,沟沟壑壑的地方都记得,能画出图来。
在国民党部队当兵,这孩子只回来过一次,戴着个大檐帽,打着三角皮带,蹬着大头鞋,好不神气。那些没当上兵的,没有不后悔的。
后来,孩子所在的这支部队,在上饶(一说在井冈山)和人民军队打了一仗,死得只剩下千把人了。这支部队以前就和人民军队交过手,是“有血债的”。师长这人极其刚烈,最后下令:上过战场的,都跟我冲;没拿过枪的,等我们死完了,出去投降。
这孩子,后来就成了人民子弟兵,转行当了工程兵,还有点职务,比排长小一点,具体就不知道了。
这人要是走运,真是什么都挡不住。一次,他正指挥二三十个人修桥,正好有一个“不得了的大的首长”经过,看到这孩子指挥修桥,二三十个人,没有闲着的,没有碍事的,做事井井有条,剩了几小块木板,都整整齐齐摞起来放在路边。
首长很是高兴,派了个警卫员下车,问了孩子的番号和姓名。不久,嘉奖令就下来了,孩子一下被提到了副连级。
后来,这孩子以正连级转业,也是做工程方面。
他在部队官当得不大,正连级也只是名义,没有什么实权。但他讲义气,会交朋友。在部队,领导喜欢,战友信任;在工作岗位,也是非常得人心。
五十六七岁的时候,正好遇上改革开放,办了个病退,拉了一批人,搞起建筑来,后来又做建材,办了好几个公司,赚的“钱都不当钱了”。
据传,上世纪九十年代,资产就上亿,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有两个女儿——至少我们那人这么认为。
这孩子(姑且这么称呼吧),不管谁站在他面前,都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也没听他曾立下多大的志愿,也算是随命运逐流的人,能累积巨额财富,恐怕是因为相貌出众,受上天垂爱吧!
一年正月,章公在我们那附近走亲戚。吃完饭,天气正好,一群人就在屋檐下晒太阳。不知道谁提议:章公,反正您坐在这也没事,就帮我们看看相吧。
章公喝了点酒,有点微醺,兴致很高,把凳子一横,一坐定,说:“看就来看一下!”
正好一个人挑了担牛粪去施肥,章公打招呼说:“某某,这么勤快,大正月就做事!”
这人就把牛粪放下,说:“章公,难得你开金口,今就先帮我看一下哟。”
章公也不推辞,拉过挑牛粪的人,说:“今我吃醉了,要乱说,你莫生气,当我打乱话(胡说),后生呀,这人呀,得闲时就要闲哟,你这人,一辈子劳累啊!”
挑牛粪的人笑笑,说:“我们这些作田的,都是牛一样,哪个不累?”
章公说:“老侄,你和人家不一样,你是‘落雨担杆(干稻草),担水浇沙田’的命哟!”
挑粪的人问道:“章公,这是什么命哟?”
“什么命?”章公沉吟了一下,“你看,这六月天担杆,下起雨来,杆越来越重!你是走快了累,走慢了也是累;担水去浇沙田,不管你担几多,都浇不满。”
这挑牛粪的人也是比较开朗的人,淡淡地说:“这样说,我这牛粪还去挑什么?也坐在这晒日头算了。”
章公一摆手:“这命里注定了,你逃得过?你去看,有的人屋里钱没一个,每日哼着曲子,过得快快乐乐;有的人,屋里的钱,几世都用不完,每日还是愁眉苦脸,过得劳劳碌碌。莫怕命不好,都只有这几十年,莫想不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一世人。”
挑牛粪的人正要再问,一个后生挤了进来。
这后生姓李,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去世了,跟哥哥生活了两年后独立出来了。他本来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做事是“一把好手”。因为没有人管,慢慢地变得不愿意做事了,用我们这话来说是“歇懒了”。
断粮的时候,经常向大家去借(当然也会还的),算是有一天过一天了。
人穷志短,也没什么脾气,谁都能说他几句,他偶尔才辩解几句。什么事情都是笑笑就过去了。我们这人都叫他“赖皮”(介于不要脸和自尊心不强之间),当然,也是戏谑的说法,没有多大的恶意。
“赖皮”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虽然过得艰苦,但也还算惬意。他并不奢望日后能怎样,之所以挤进来,是因为想博人一笑——人的内心总是寂寞了的,正面不能受到关注,装疯卖傻,能引起人注意,也能得到内心的慰藉吧。
“赖皮”还没有开口,旁边的人就笑了:你还看什么相?有一个人就起哄:“‘赖皮’,你这相还要章公看?我都看得出,你是‘吃倒和尚住倒庙(得过且过)’,有早饭不抄(愁)夜饭的人。你这一世,过得比狗都快活(方言,每天悠哉悠哉的样子)!”
这人一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赖皮”也不生气,对着章公说:“公公(对年纪大的人尊称),别的我就不求,我只想问一下,我有老婆讨么?莫把我屋里这点香火断了。”
章公并不回答,而是扭头对刚才起哄的那个人说:“后生,你莫说我倚老卖老哦,‘老本人言’,老了没用是真没用,有钱有势莫欺少年!”,然后,又指着“赖皮”说:“这个冒失鬼(长辈对晚辈昵称),十几岁的‘青皮后生’,别看他懒,他独独生了一副好相貌!”
起哄这人,和人聊天,喜欢“争赢事”(没理的说成有理),被章公说了,心里不舒服。他不敢和章公争辩,只是嘀咕:“这赖皮要是有用,我们姓李的就不怕没人了(这人和赖皮同宗)!”
章公没理起哄的人,拉了“赖皮”的手,握了握,又摆了两下(在我们这是友好的动作),赞叹说:“这真是一个好后生,真蛮好!”,说完,又对着围观的人说:“今我就来‘显显道艺’,而今这么多人在这,日后你们来做个证,看我姓章的是有本事还是‘好高’的!”
有好(四声)事的人,就问:“章公,你说他相貌蛮好,他到底哪里生得好呢?”
章公举起左手,点了几下说:“这后生的相貌,是有诗为证的哟!”
还有诗?围观的人一下都有点激动了,纷纷问:“什么诗?”
“世间六月火烧天,地上男女哪得闲?黄牛累得气哼哼,独有闲人来摇扇。”
“闲人一摇芭蕉扇,屋里金银有得捡。上天下海有人在,不比前世多修来。”
章公念诗的时候,摇头摆脑,很是沉醉的样子。念完,又解释说:“这后生,带了前世的金银过来,他而今是什么都不想做,这就是他的命,他不做有得吃!他呀,还不光有吃,还比我们过得好,等他寻到了他前世带来的东西,我们这些人,哼哼,看到他,人家愿意点个头,是他的礼节,他就是板起脸来,还有人去拍他的马屁!”
章公一说完,周围热闹起来了,都说章公喝醉了,乱说话。
只有“赖皮”很高兴,对着章公说:“公公,要是你看得准,我逢年过节都要去买块肉给你!”
章公只是摇头:“我还活得到那时?你要是有情谊,七月给我烧几块纸,都是你的心意。”
“赖皮”脸一红,发誓说:“我真有这一天,每年七月给你‘一头’(用竹子编的筐,量很多,表示隆重),不烧我是我是狗操的!”
章公笑而不语。
虽然章公预言“赖皮”必定有大成,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赖皮”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观,依旧是得过且过,过着“赖皮日子”。
一晃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赖皮”已经三十出头了。农村不比城市,有“大叔”这个概念,农村男人三十还没有娶妻生子,基本宣告注定一辈子光棍了。
当时,国家实施“包产到户”的政策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是如何包产的,我们这,基本上是以组单位(我们这叫队),照解放前的总量进行平均分配的——也就是说,你们组上,解放前所有人拥有的田地、山林加在一起,除以人数平均分配。
现在农村的土地,似乎也没有多少珍贵,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田地、山林是农村的人的命根子,是“千百年祖业”。“包产”分配的时候,大家都是“寸土不让”的。
我们组上,有一块山林,面积很大,有近三百亩,离我们那有四十多里路程,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女子带来的嫁妆。因为路程太远,根本没有办法管理,因而,被当地的人砍得不成样子,基本没有成才的木材,全是茅草。并且,这山石头很多,土薄,树木很难长起来。
分山的时候,这地方就成了个问题——没有人愿意要。没办法,队长想了个办法,把这块山林作为一份(得这山林的人不参与分配了)。这山面积虽然大,没有出产,谁愿意要?商量来商量去,只能抓阄了。
抓阄这方法,最公平又最不公平,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只能如此了。
一抓,这山林被我们那一户姓王的人家抓住了。这家男主人,本来是很大度的,生死都有命,何况一点山林?但把纸条拿到手里端一详,发现纸上有指甲痕。把别人的拿来看,又没有——明显是队长做了记号。王姓这人,最受不得欺负,一下子怒火中烧,把桌子一掀,骂道:“分我的卵!”
王姓男子有五兄弟,“打虎亲兄弟”。自己的兄弟受了欺负,兄弟哪有不出手的道理,几个人一拥而上,要队长给个说法。其余的人,都担心要是重新抓阄的话,会被自己抓住,所以,只是都在解释:这是队长裁纸的时候无意弄到的。
王姓几兄弟,个个人高马大,哪里怕得罪人,最小的一个,脾气比较急,抄了一根扁担,朝着队长劈了过去。还好旁边有个人眼疾手快,用凳子挡了一下,队长才逃过一劫。队长这边也有好几兄弟,一下子被激怒了,也纷纷准备动手。还好人多,大家把人拉住了。虽然被拉住了,但对骂肯定少不了的。一时间鸡飞狗跳,大家都手足无措了。
“赖皮”突然站了出来,大声说:“吵我的屌哦,你们不要我要!我反正要绝代,没有后人会骂!”
吵架双方虽然吵得厉害,终究是为了利益,现在有个“二五八的人”(不聪明,傻的意思)愿要,吵架的基础就没有了。零零星星争了几句,就定下来了。
分完后,“赖皮”兄弟骂道:“你就是一个猪脑壳!”——兄弟认为“赖皮”必定没有老婆讨,等他死了,山林自然是自己儿子的了。
“赖皮”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的走了。
以前农村的生活,靠的就是几块稻田,一点山林维持生计。有一段时间,竹子、木头的价格比较高,有山林的人家,慢慢都“富”了起来。只有“赖皮”,日子过得紧巴巴。
《水浒传》里讲“三十不娶,不应再娶;四十不仕,不应再仕”,“赖皮”四十多的时候,仍是孤身一人,家徒四壁。
如此种种,基本预示着“赖皮”的人生命运走向——一个在孤独中走向毁灭的农民。
谁知道,命运忽然来了个大转折。
我们这盛产(似乎也不算)稀有金属,有一段时间,似乎是允许私人开矿的,合不合法就不得而知了。一探测,“赖皮”分的那座山上,居然有钨矿,等分还很高。
一时间,找“赖皮”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最终,“赖皮”以每亩五万元的价格“卖掉”(转让)了一百三十几亩山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为这事,“赖皮”组上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讨论山林所有权的问题。争了很久,村里镇上才做出决定:拿出百分之五归生产队共同所有。
“赖皮”这人,虽然不愿做事,但还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没有头脑发热,花天酒地。买了一辆“东风”,跑起运输来。
运输跑了几年,往工地拉砖拉得多,和搞建筑的老板慢慢熟了,不知道怎么又搞起了房地产。世纪之交的时候搞房地产,接下来的事情,我不说大家也能想象。
据给“赖皮”做过事的人来讲,他做这么大的生意,但从不记账(他不敢接大项目)。人家给他做事该给多少钱,全靠记忆。结账的时候,多是“算成一下(相差不多就可以)”。
客观上讲,“赖皮”在我们这,不过“中等人”,但穷困潦倒时候,没有怨色;春风得意的时候,循规蹈矩,也算一奇吧。
若说人生圆满,“赖皮”应该能算一个。
章公虽然没有学到“倒山”功夫,但他在武术方面的造诣,在我们那,也是“有算”(排得上名次的)。他这人,爱打抱不平,为人正直,处事公正。
在解放前,我们那一块(一带)有了矛盾,争执不下的时候,都会请他去“摆事”——判断是非曲直。章公平时脾气较急,但摆起事来,那是苦口婆心,从不强迫某一方接受,都是要双方心服口服才会放心。大家乐意接受他的判定,因而威信很高。
中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被自己的一个徒弟接到家中传授武功——相当是供养起来。
他这徒弟,是我们临县的一个大地主。章公在他家,确实过了一段“享福的日子”——据他说,是餐餐(顿顿)有荤,出门有人抬轿,洗澡都有人端好水。
因为这段历史,他在“文革”时候,还受了点波折。幸好这时他年纪很大,家里也没有什么产业,在农民之中,也只能算中等,因而没受多大的苦。
虽然没有受多大的苦,但他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愤愤不平。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感慨呢?因为“文革”初期,工作组展开工作的时候,有人举报章公。这些人之中,有的是章公曾经救治过的。
最让章公寒心的是我们那儿的一个人。
这人在“文革”初期,因为工作认真,非常受领导重视,从一个民兵队长提到了乡里工作,而且是“到市里开过会的人”,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人”。
“红人”七八岁的时候,曾从十几米高的板栗树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左腿小腿骨完全折断,骨头都把皮“撑起来了”,所有人都说这孩子没救了。孩子母亲哭着把他背到章公家里,章公看孩子“造孽(可怜)”,二话没说,答应救治。
在救治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孩子内伤太严重,用章公家祖传的药草,怕“到不了功(药力不够)”,孩子治好了,也是个废人。
当时,我们那治内伤,彭家最擅长。不过,“是药三分毒”,治内伤的药更是如此,因为里面有几种药草,本身就是毒药,“制(好像是蒸熟后暴晒,降低药的毒性,我不懂)”的时候,必定要亲力亲为,心中才会有底,因而非常耗人工。治内伤,不光要懂药理,更要经验——草药在剂量方面本来就很模糊,稍不留意,治病就会变成“止命(毒死)”。
彭家治内伤的药,向来只救治自己“姓上的人(同一家族的人)”,外人无论怎么求,都没有用——主要也是怕出医疗事故。
章公没办法,只能对彭家懂药草的人说:“你不是想学‘接斗(治疗骨折方面)’么?你治一下这小孩,我把它传给你!”
这“接斗”道艺,是章家祖传,在我们那,是独门秘技。别的人治疗骨折,特别是骨头断了的,患者都是痛得“哭爷喊娘”。章家的方法,患者只会痛几下——都是章公和他聊天,忽然间出手,等人反应过来,疼痛感就消失得差不多了。经章公家族治疗过的,没有人成残疾。在医疗条件不好的时期,想学章公这“道艺”的,不知道有多少。这话一出,彭家的人才答应救治小孩。
谁知道,在一次批斗会中,这“红人”忽然站到了台上,大声喊:“去把那个老章捉得来‘陪斗’!”说完,带了群后生直奔章家,把章公拉到了村委会。章公算是经过事的人,但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能乖乖就范。
毕竟都是本乡本土的,章公这么大年纪,往台上一站,大家都想:“怎么把人家章公搞来斗?”
“红人”一看下面没声音,就挥起拳头高声说:“这个老章,解放前,摆起事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奉承那些有钱有势的,不晓得得了几多钱!你们不晓得吧?他到某某地方,哪里是去教武功?他是去帮地主当打手,不晓得‘讹(欺负)’了几多老百姓,这样的人,还不要拉得来斗?”说完,拿了一个“高帽子”(据说,是用纸糊的,有两尺来高)往章公头上一罩。
中国的农民压抑得太久了,被‘讹’的滋味,感同身受,一下子,气氛就被调动起来了。
章公性格本来就烈,开始是怕牵连后人,一直忍着,现在把帽子戴上了,哪里忍得住?眼一横,骂道:“今我就‘舞(弄)’死你!”,说完,两手“一盘”,“红人”一下子就退了好几步。
“红人”顿时“红了眼(发火)”,大声说:“我晓得你有几下,今你还做得了怪(能怎么样)?你敢打我么?打了我,你就是个‘反革命’!”
以前,民兵训练很受重视,我们那一个小小的村,有十几个民兵,训练都是真枪实弹。我小时候还见过重型机关枪的子弹,过了一二十年,还是黄灿灿的。
批斗会上,民兵都是荷枪实弹站岗的,十几二十岁的“青皮后生”,就怕没事,一听有“反革命”,都端了枪指向批斗台上。
章公却不怕,骂了起来:“‘卖*的子(骂人的话,字面意思是妓女的儿子)’,我八十几了,今就去死都比别人多活了几岁!你说,我奉承了哪个有钱有势的人?而今见证过的人还没死尽吧?我今赌个誓愿,我要是收了人家一分钱,我屋里死绝!你说我在某某地方‘讹’了老百姓,你找个证人出来,对个面(对质),只要有一个,今我就死到你面前!”
“红人”平时斗的,都是些“地主”,早被吓得畏畏缩缩了,像田里的泥巴一样,要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碰到反抗这么激烈的,还是第一次,顿时没了主意。不过“红人”能“蹿得这么快(升官很快,贬义)”,也是有点本事的,立马转向,大叫:“你敢骂党员?来!捆起来关到(关起来)!”
还好,有几个年纪大的,和章公关系好,就劝“红人”:“这个老章,年纪大了,‘发懵(神经病)了,莫跟他一般见识!’”
“红人”刚才受了章公一下,怕被“下手(点穴)”;再说,自己这么有前途,万一章公“发猛(不顾后果,采取极端方式)”,跟自己拼命,不值得。因而,卖了个乖:“我乡里还有会(要开会),你们再斗!”说完,骑了自行车走了。
这人,要是不怕死,什么事情都好做了。章公看“红人”要走,把帽子一摔,跺了几脚,故意对着红人说:“‘上台的官,下台的狗’,你这个人不遭报应,我眼珠挖给狗吃!”
台下一下子乱了,批斗会成了骂人会,大家嬉笑起来。
章公一家人,也跟着到了批斗会场,在台下都是胆战心惊,冷汗直冒,一见“红人”走了,忙上台去扶章公。
章公却不肯下去,在台上骂起来:“这个‘没眼珠的(忘恩负义)’,不是我,他活得到而今?胎都投了几次了!而今倒过来搞我,他要是会死在床上,我章字倒过来写!”
这时,章公的孙子也快三十了,在回家路上,劝章公:“公公,而今这世道,你莫乱话事(说话)呀!我们而今怎么搞得人家(红人)赢?人家一句话,我们屋里这日子就过不成了!”
章公“哼”了声:“这个‘背时鬼’莫怕!他‘红(我们称春风得意为红)’不得几年,苦日子还有的过!”
章公家,气氛非常和谐,孙子就笑祖父说:“公公,人家说你看相蛮准,我看你也是乱扯,你要是会看,那个时候不给他治,哪里会受今(天)这样的气?”
说完,一家人都笑了起来。
章公叹了口气:“他这相貌,我还看不到?他天生一副‘反像’,人家说‘翻眼就不认人’,他是当面都不认人的人!哪个晓得他会来搞我?”
大家都认为章公是说气话,也没在意。
章公又接着说:“你们莫笑,他——我看得准,今我为啥子敢发火呢?这个人,心里蛮恶,不过没‘杀心’,这样的人还当得了官?他只做得‘差狗子(听人使唤的人)’。别看他而今响当当,他有‘落劫(遭难)’的日子,他是‘石头滚下岭,哭都哭不醒’!”
章公儿子这时也插话了:“爷老子,怪不得你寿命长,你这个人心宽。人家还石头滚下岭?而今我们屋里,真是‘泥菩萨过江’哟!”
章公也不恼,说:“什么心宽不心宽,我是看得到事(能预测),你们看,这个‘背时鬼’只有这几年好运,有他‘乌面(落魄,灰头土脸)’的时候!”
反正也是闲聊,孙子就反驳说:“他还会‘乌面’?人家而今都去的了市里开会!”
章公点了筒烟,吸了两口,说:“他不光要‘落劫’,寿命还不长!死的时候,是‘喊娘叫爷’!”
一家人闲聊,谁也没当真。
谁知道,“红人”的命运真如章公预测一般。
“红人”这人,斗起人来,六亲不认,得罪了很多人。“文革”还没结束,赏识他的领导也被人斗下去了,“红人”是这个领导树立的一个典型,自然逃不过牵连。
有一个“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起来了”。据说,他曾直言不讳对身边的人说:“我坐这两年牢,哪个都不怨,就是想到某某(红人),硬是牙齿都是酸的!我不搞翻他来,死都不心安!”
墙倒众人推,“红人”一下子“遭了难”。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反正是在一年过年前,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判了八年。
牢没坐满,“文革”结束后就放了出来。
还没出狱,他老婆早带着两个女儿改嫁了,父母过世,兄弟不认,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单身”。
开始,村里基本没人理他,后来慢慢好一点,但心中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隔膜。
可能在牢里把身体搞垮了,“红人”回来后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而生活很困难。
七八年后,不知道怎么就瘫在床上了——下身不能动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他的两个亲生女儿和他不亲近,又嫁得远,只是偶尔回来服侍一下。其余时间,都是他的侄子或邻居,盛了饭,放在他床头。
因为动弹不得,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房间臭气冲天,没有人愿意进去,后来都是从窗子里把饭伸进去。
这样,在床上“赖”了两年。
一天,有人发现他滚到了地上,一叫,没反应——死了。至于是病死,还是冻死,没人知道。
盛殓的时候,大家看着也是流泪:头上虱子到处乱爬;背上的皮几乎全没了,露出红通通的肉;大腿两处化脓的地方,长满了蛆。
在为章公的相术称奇的时候,也为“红人”悲哀。也许,他真的没做错什么——在时代的车轮之下,哪会有完整的人?也许,只有幸运和不幸运的人吧。
人生艰难,幸与不幸,都是命,多点仁爱恻隐之心,也算是积福吧!
因为“红人”的事情,章公有点意兴阑珊,帮人治病,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热心了。把祖训改了一下,治病也要看人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兴起了一阵练武的热潮——也许是受了武侠电影的影响。
我们那的武术,多是家族传承。师傅传授武功,称之为“开攥(音)”,没有太严格的师徒关系,多是家族中的长辈,带几个或十来个后辈,一方面,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传承“家学”。教武功和学武功,都是增强日趋淡薄的家族关系的手段。
我们这,以前多是聚族而居,基本上,人口较多的姓,都有自己家传武功,至于武术源头,大多都茫然不可考了。
传统的武术和现代搏击不同,是“不好比”的。按我们这的说法:练拳、站桩、耍棍之类的,都是“硬柴功夫”,打起来虎虎生风,好看,但没有什么用处。真正的“武功”,都是只有“几下功夫”,出手,没有放倒对手,就算是技不如人。
这“几下功夫”,不是攻人要害,就是“下恶手”——点穴之类的。真要比起来,就不好分胜负了,比方说,你把我打得起不来了,但我已经“下了手”,你最终要丢命,算谁赢?
虽然不好比,但哪门功夫厉害,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多是在友好的氛围下“试手(比试)”,几个回合下来,谁强谁弱,大家心知肚明。
一时间,刘姓、周姓、王姓、彭姓等较大家族,都“开攥”了。
在“严打”前,我们那农村,还是比较“尚武”的。学武功的年轻人多了,免不得有些纷争,“会几下”既是个人光荣,也是家族的荣耀。年轻人,难免争强好胜,多认为自己所学的厉害。但即便打遍附近无敌手,没和章公家族的人交过手,仍不敢称第一。
令人遗憾的是,章公两个儿子及孙子,都是“吃国家饭的”——国有企业职工,成了城里人,很少回家。
章公的老婆,在他八十多一点的时候就去世了。章公的儿子和孙子,都是孝顺的人,几次硬把章公接到城里“享福”。用章公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条“贱命”,在城里,像关狗一样关着,“一天不得夜(时间长,难熬)”。住不了三天,就“起病(生病)”,儿子孙子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找了个七十几岁的婆婆,算是“作伴”。
我们那有一段时间,兴起“种草籽(一种肥田的植物)”,是行政命令,家家户户必须执行。不知道是出于好意还是别的原因,为了保护草籽,特别成立了“联防队”。发现有鸡鸭之类的下田,抓住了就要罚款,不交的,鸡鸭就没收。
农村人,没有多少法律意识,行政命令,就是法律,即便自家的鸡鸭进到自己的田地里,照样罚款。
“联防队”的成员,多是些“青皮后生”,年轻人在一起,事情总是多些。
这些年轻人,多是练了几下的,破坏性比一般年轻人又多一些。自己几个人,比得没什么意思了。一天,一个人提议:“只听得说章公屋里的道艺不得了的好,不晓得到底有几厉害,要去试一下就好!”
章公这时已经九十多了,他的那些光辉事迹,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有个人就嘲笑提议的人:“他死都快死了,还有几厉害?我有半只手(只用半只手),他都不知道‘跌到哪去了(意思是被摔很远)’!”
提议的人也不服气:“你一个猴子样的,好什么高(吹牛)!你搞得章公赢,我买两条烟给你,你要是没搞赢呢?”
“没搞赢我买十条烟给你!”这人有点被激怒了。
年轻人,就怕杠上,一杠上,事情就复杂了,不分个输赢就不能罢休。周围的人一起哄,两人就决定要试试。
问题是怎么让章公出手了。“联防队”的队长也是个好事的人,说:“你们一个人买包烟给我,我就有办法!”
两个年轻人,也是较劲,还真去买了烟。
队长这才说出了他的计划:趁章公不在家的时候,把他家的鸡放出来,然后他们把鸡抓了,章公不出手,鸡就不还给他。
没想到,当天下午,他们还真是找到了机会——趁章公“两老祖(年纪大的夫妻)”去捡柴的时候,把他们关鸡的房子(一般是猪圈)的门打开来,一群人在田边等着,派一个人去放哨,看章公回家了,就开始抓鸡。
章公一到家,看到“联防队”的后生都蹲在自己家门口,就笑着问:“你们来我屋里吃夜饭?”
队长装作一本正经,指着被捆起来的二十来只鸡说:“章公,这是你屋里的鸡吧?我们都在这等你回来!”
章公年纪虽老,但不聋不哑,思维清晰,一看,大惊:“我记得出门的时候关起来了!”
“联防队”中的一个人故意大声说:“你老了,记成昨日了吧!”
章公一脸疑惑,队长接话了:“章公,这怎么搞?我是想算了,不过呢,放了你的鸡,别的‘社员(村民)’就有事(话)说了!”
“这怎么搞?”章公自言自语。
队长趁机说:“章公,我们这有个不服气的人,刚(才)在这说,你老了,搞不他赢,要是你搞赢了他,他把罚款的钱出了!”
章公笑了起来,说:“这个后生说得没错啊,人家说半个身子到土里了,我是只剩下半个脑壳在地上,还搞得谁赢?”
队长一看不行,就把想和章公交手的人拉过来,指着另一个(打赌的人),对章公说:“这两个‘冒失鬼’,吃饱了没事做,打赌,赌十条烟!”
队长也是试试,其实心里已觉得交手希望几乎为零了,毕竟,章公这么老了。
谁知道,章公慢条斯理说:“有这回事?十条烟,分我一半么?”
大家一看有希望,都说:“有!有!你要是搞赢了,今在这的,还要一个人买条烟给你!”
章公爽快地说:“试就来试一下哟!就在这试一下!”
大家见章公这么不服老,都来了精神,纷纷让开地方,围成一圈。
章公对交手的后生说:“后生,我老了,没你这样的精神,我讲好,你倒了地(倒在地上)就算输,做得么?”
年轻人自然答应。
对手是一个九十几的人,年轻人自然不敢用“狠劲”,张开双手冲了过去,打算把章公抱紧,章公动弹不得,自然算输了。
哪知道,章公还很灵活,“卖了个身(转身躲过)”,用手掌在年轻人脖子上(背后)轻轻一拍,年轻人“忽”的一下,踉跄两步,一晃,整个人就瘫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其他的人,以为年轻人“装死”,也没去扶,过了几秒,才看到年轻人面色铁青,口里开始冒泡了。顿时吓得不得了,连忙叫章公:“章公,章公!你不是下了‘杀手’吧?”
章公一拍手,笑笑说:“耍两下,还出得了手?没事,他‘停(休息)一下’就好了!”
过了两三分钟,年轻人才顺过气来,站起来,竖起大拇指,说:“章公,你是有道艺,我是‘挨不了你的青(沾边都沾不到,形容差距极大)’!”
在场的人,没有不服的,香烟的承诺,都“兑了现”。
据这个年轻人讲,当时,他感觉有一根棍子狠狠地敲在他脖子上,眼睛一黑,接下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章公用的,到底是邪术功夫,还是武术,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年轻人,我认识,现在五十岁不到,我和他一起打过牌。虽然“证据确凿”,但我仍是半信半疑——章公比不过他父亲,章公能随便一拍,就让人丧失反抗能力,那他父亲,岂不是能随随便便致人于死地?世间,真有这么厉害的武功,那岂不是和武侠小说写的差不多?
这个故事,和麻衣相术没任何关系,不管怎么样,先记录下来吧!
小贴士:
其实吧,鼓励只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动动小手,点个“赞+关注”,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