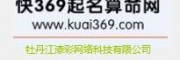第63期主持人 | 徐鲁青
我在大理结识的第一个人,在认识几个小时后就提出要给我“看看盘”。她在APP里填上我的生辰、性别、所在地,几秒后,她的微笑有些凝滞,“你上升星座处女?”
“不会吧。”我虚了,隐隐记得几年前测过一次,肯定不会是处女。资料里唯一改变的是所在地,果然,如果那一栏填老家,我的上升星座就是水瓶。也就是说,如果我之后一直在上海,三十岁之后会越来越像处女座?
这让我想到周奇墨的一个段子:一个人生在5月20号,就是专一的金牛座,生在5月21号,就是渣男双子座,“这就让人觉得,他一定是5月20号晚上想明白了什么。”
星座、八字、塔罗和心理测验等流派的信奉者们有时还会互相印证:“果然,你们双子座都是INFP,所以你会抽到这张女祭司牌。”无论是外国玄学还是本土玄学,很多人似乎都是要信一信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哲学里有一些关于算命的学理反驳,最有名的一条悖论是:既然算命了,那肯定是认同宿命论,但真正认同宿命论的人不会妄想自己能改变命运,所以也是不会去算命的。
这也太刻板学究了,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含混又矛盾的半吊子宿命论者。有的玄学是实用主义的,比如紫薇斗数,围绕婚姻、子女、财富、福德看运势,为人们提供下一步要怎么走的建议。更多时候人不是想改命,不过是希望了解自己,或者只是想倾诉罢了。讨论星盘时会自然而然滑入深度交流,塔罗牌既像神秘仪式也能创造冥想时刻,它们甚至仿佛另一种方式的心理治疗。在塔罗牌测试里,向占卜师描述困境,并听到占卜师的回应,或许都能让信众的情绪有所好转。毕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的数据,中国每10万人才拥有1.5名心理医生。与之相比,一副塔罗牌和一次MBTI测试,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更触手可及。
在你们看来,为什么一些人喜欢谈论玄学?
01 玄学是解释世界或宽慰自己吗?
潘文捷:对星座抱有疑惑态度是从参加天文社团后开始的。十二星座来源于黄道十二宫,意思就是说,从地球看,太阳一直在这十二星座之间移动。问题在于,星星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2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把蛇夫座也列入其中,现在黄道上实际上有13个星座。所以即使十二星座说真的有道理,那么它现在也算是非常不精确的了吧。
吃核桃能补脑,生吞蝌蚪能促进精子发育,天上的星星中写满了我们的命运。福柯在《词与物》里看到,这种根据相似性组织符号运作的做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那时候,知识来源于魔术和博学。听起来是不是和我们传统中的吃啥补啥、以形补形异曲同工?事物之间遥远的相似性确实充满了谜之魅力。
林子人:医疗史学者发现,大流行病会在人群中引发规模颇大且耐人寻味的反应,其中之一就是宗教狂热。《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一书中讲述了两个例子:中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欧洲人将这一致死病魔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人们纷纷祈祷、举办宗教仪式、在门柱上放十字架;还有一类被称为“鞭笞者”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出现,他们在道路上一边行走,一边用铁链和带钉子的鞭子鞭打自己,直到流血为止,以惩罚自己的方式承担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天花的破坏力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全世界各地许多宗教都创造了专门针对天花的神祇、女神或圣人。鉴于新冠大流行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一些人会转向宗教或广义的玄学寻求帮助也是意料之中的吧。
在首次出版于2005年的《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一书中,美国记者、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发现,求职培训教练和广大雇主都在宣传MBTI性格测验,尽管研究发现该测验毫无科学可信度——在一项研究中,测试者中只有47%第二次测试得出同一类型;另一项测试则发现,数周或数年后再测,测试者中有39%-76%的人变成了不同类型。
艾伦瑞克认为,企业喜欢用人格测验来评估和筛选人才,其实是为了把员工满意度的责任推卸到“契合度”这只替罪羊身上,让被拒或解雇有合理化的解释。艾伦瑞克还发现,一种“基督教商业文化”在美国欣欣向荣,一些大型企业内部出现了员工祷告团体,越来越多企业公开宣布基督教为其企业价值观,同时有越来越多失业人士参加教会活动。
人性大概就是这样,虽然神灵已被祛魅,但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面前,现代和理性又似乎不敌孤独和恐惧。当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不一定有效,我们不得不费劲地去找到一个新的解释来理解世界。那么我们会怎么办呢?正如艾伦瑞克所说:“你要不就是去寻找塑造你生活的体制性力量,要不就是把你职业生涯中不可预测的起起伏伏归之于一个力量无限、永远关照每件小事的上帝。”
叶青:10岁前记得的事情不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玄学有关。小时候家里人带我去算命,说我3岁、6岁、9岁都会有“水灾”,要小心。前两次居然都灵验了!尤其是6岁时不小心失足掉进了井里,幸亏旁边有人把我捞了上来,让我特别后怕。过完8岁的最后一天后,我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绝不靠近有水的地方,平安地度过了9岁。
当然现在回看,前两次水灾与其说是灵验,不如说是注定。我从小就特别爱玩水,小孩在水源旁边玩耍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新闻中的类似事故层出不穷。算命先生给出这类预言,大抵也是为了让家长多留个心眼,倒不是真的有什么预知未来的本事。
与之同理,许多人将期待投向玄学,也不一定是真的相信存在神秘力量,更多时候是想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像是中国台湾地区盛行的“观落阴”和西方的“灵媒”,都是通过某种媒介让生者与死去的亲人进行对话,询问他们在“另一边”是否安好,有没有什么未竟之事。得知逝者一切安好或完成他们的夙愿,得到宽慰的自然是生者。
在最新一集的《白莲花度假村》中,谭雅怀疑丈夫有了外遇,找来一位“吉普赛”灵媒。初见面时,因为灵媒的穿着颇符合刻板印象,谭雅称赞她一看就“靠谱(real deal)”,但当灵媒如实解读塔罗牌的预示时,谭雅却崩溃了,因为牌面证实了她关于丈夫的猜想,而她找灵媒恰恰不是为了听真话,是想听让她能暂时舒缓的“假话”。谭雅歇斯底里地将这位可怜的灵媒赶出酒店房间,一边大叫道,“你太负面了(so negative),太负面了!”
02 玄学是实用主义或自我探索吗?
尹清露:我对玄学蛮感兴趣的,起初是因为好玩,就像Lana Del Rey的那句歌词唱的:“我的月亮星座是狮子,太阳是巨蟹,啊你不信这个?你可真没劲。(You wont play, youre no fun.)”后来自己学了点三脚猫的占星知识(对,还买了那套《内在的天空》和《人生的十二个面向》),故作神秘地给朋友们看星盘,也享受过别人说“哇塞好准”——其实如果星盘命理有一套语法,我也就将将背会单词的程度,不过,毕竟这套体系本身庞大而坚不可摧,挖点边角料也足够用了。
徐鲁青:唯物主义逻辑得当,但却不如神秘充满魅力,许多作家会信玄学,卡波特从来不住13号房间,从来不在周五结束和开始工作(那他周五到底在干嘛?),狄更斯在睡觉的时候会坚持朝着北方。作家骆以军也很信玄学,最倒霉的时候他会重金找命理大师算命,星座只是上学的时候玩玩, “主要是为了把妹。”他认为星座跟紫微斗数完全不一样,更多在描述人,而不是像八字那样去聊将来有没有成就。我觉得这个区分挺有意思。
尹清露:现在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情绪,一部分人觉得现实生活没有什么能全然相信,于是要借助玄学,如同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是为什么恋爱是占星的亘古话题,因为爱情本来就不属于“努力就有回报”的逻辑。就像马克斯·韦伯曾说的那样,所有人都认识到了期望和经验之间的差异,都会对意义怀有潜在的渴望。
难道这是一种宿命论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不仅是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命理市场也很兴盛,比如许多国内企业家会信奉六爻预测中的经济学理论(更别提在公司供奉财神等等),但即使是相信玄学,也并没有阻止他们渴望创业成功啊。
我之前读到过人类学内部对命理的一个定义:malleable fixity,也就是“可塑造的固定性”——命运一方面是崇高不变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所更改。用阴阳五行的话来说,金木水火土统统都是一种“象”,而“象”并不拥有本质,它附着在不同事物上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一个人的“木”元素比较重,可能说明他做事比较有条理,就像逐渐开花结果的树木,也可能意味着他给人一种春天般舒适的感觉,而这些“可变化的意义”是可以在对话中形成的。
所以在中国,虽然存在着一套复杂而古老的算命体系,但无论是专家还是非专家,都不太可能就某人的命运达成完全一致的判断,更何况我们还有“流年”的概念,这十年运气不好,下十年换个大限运气就好了嘛,总归是祸福相依的。而如果只注重“准不准”,那才是落入了“术数”的桎梏,变成庸俗的宿命论者了。
我觉得,一些人热衷于算命,甚至把占星师看作另一个心理医生,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也会发现,所有关于命运的故事都是一种“自我陈述”,而不是以教义的形式出现。人们感到绝望、觉得自己可能受制于一种更大的力量,但有时候,恰好是对“命运”的觉醒迫使他积极地和这种力量打交道,希望在算命的过程中得到点什么,在信和不信之间、犹疑和恍然之间做出决定,再一步一步地生活下去。这个过程本身,就十分动人啊。
徐鲁青:“自我陈述”这点好有意思!我在塔罗牌体验里也有感受到,比如在用塔罗看人格的时候,会抽三张代表我不同层面人格的卡牌,画面里充斥着意涵丰富的物件符号。我、塔罗师、围拢看牌的朋友们会一起讨论它们的意义,有些会注意到人物眼神的方向、人与周遭物的关系,有的人会说画面结构、颜色以及三张牌的对比,我们知道有无数个角度可以入手诠释。在对话过程里形成的,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叙述”,那些卡牌和画面则是诱发叙述的引子,于是我的人格特质在讲述里自然而然清晰了起来。
尹清露:是这样的,我也去测过塔罗牌,不过我对这个形式还是有点疑惑!可能因为一切都太过于“一念之间”了吧
董子琪:中国台湾地区流行紫微斗数,唐诺在书里应用过紫微的四化(即科禄权忌)的概念。大陆作家双雪涛在小说里也分析过八字。《金瓶梅》里有术士上门给西门庆的几位妻妾算过命。其实,《红楼梦》的群芳夜宴解花签也算是一种占卜嘛。占卜辞令一定是富有文学性的,而这种以星(紫微)、五行、花朵概括命运的方式也颇具美感。就像紫微斗数讲格局有阳梁昌禄、月朗天门、明珠出海、风流彩杖,这些名称都很美妙的。
藏在方术背后的哲学,也是可以超出玄学论命范围的,比如化权形容的是一种过度用力紧绷的状态,而化权有时候不如化禄就因为化禄轻松自在福分天成。这让我想到顾随批评诗歌所说的,诗歌用力过度是勉强,勉强就没那么美,也没那么持久,努力说到底也是一种勉强。
跳出这几种传统的论命方式,我觉得占卜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形象的人类思维,比方说数铁轨数到了单双数能意味着什么、睫毛掉了许愿能实现、打喷嚏是有人想你了、珠子断了预示着感情出问题一样,它布满了日常生活,也不止一位作家提过,但好像一般都认为只有村民村妇才保留这样的原始信仰?这种思维与文学的相通之处就在于,它相信万物之间的隐秘联系,以及人类需要保持对神秘的谦逊之心。
导语参考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0tNVnUYX8PyZPyDh7Ih1Zw
那些在玄学里找答案的年轻人
https://mp.weixin.qq.com/s/Lec4i6gc02I1_O0dU89_JQ.
把玄学挂在嘴边的年轻人,只是想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