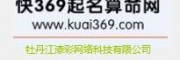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详细考辨和深入剖析,认为《梅花易数》错乱粗俗,非邵康节所作,乃明代以后从事占卜者杂抄前人占术的汇编。《梅花易数》乃江湖数术之流,而邵雍易学借易数推究阴阳变易之理,天地始终之变,属于学的范畴,二者天壤悬隔,不可同日而语。《梅花易数》企图以五行生克推论人事吉凶,从偶然性的联系作出必然性的判断,是违背逻辑规则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给人以安慰。
目前,《梅花易数》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以至于使许多人盲目崇拜,笃信不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为此,我们想就《梅花易数》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梅花易数》非邵雍所作。
《梅花易数》冠以北宋著名道学家邵康节(尧夫)的名字,被说成是邵雍的著作,果真如此吗?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宋史》。《宋史》邵雍本传记载: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是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游学四方,跨河、汾,越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旧墟,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返归河南故里。又跟随共城令李之才学习,受《河图》、《洛书》,伏羲六十四卦图象。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飞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测屡中者。道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知其道者鲜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这是本传对邵雍学业及著书的记录,并没有邵雍著《梅花易数》的文字。就是对于邵雍当时所谓“雍有玩世之意”,“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对世事皆能加以预言的传闻,《宋史》作者也认为是“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并明确断言:“雍未必然也。”
《宋史·邵伯温传》记述邵雍之子的事迹,讲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与司马光等人成为再世之交。伯温也曾论及邵雍之学,说:“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复者可忘矣。”其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周易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这里,也没有一言及《梅花易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见书籍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其中经部《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录有“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又《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观物内篇解》二卷(邵伯温编)”;子部儒家类录有“邵雍《渔樵问对》一卷”,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惟独没有所谓邵康节所著《梅花易数》。
不仅如此,我还考察了宋代与邵雍同时,而且交往密切的学者,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有关史料和著述,都没有讲过邵雍著作《梅花易数》之事;即使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所谓麻衣道者之书作过详细考证,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学的南宋易学大家朱熹,也没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梅花易数》一书的内容。《梅花易数》卷一在“占法”之后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诉世人《梅花易数》的占玩方法。但它不讲具体方法,却直接用一首诗来代替。“玩法”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仙人亦有两般话,道不虚传只在人。
此诗与邵雍《击壤集》中的《观物吟》极其相似。《观物吟》云:
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数》“玩法”系抄录《观物吟》而来,却作了改动。但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使起含义与原诗义蕴风马牛而不相及。这表明《梅花易数》的作者根本没有读懂邵雍的诗文,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原诗是说,人心具备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无两样,天道变化的法则也是人心思维的法则。《梅花易数》将“天人焉有两般义”改为“仙人亦有两般话”,将“体用”改为“造化”,就根本抹杀了邵子易学所体现的体用不离的基本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而使之堕落为占命卜的一种工具。此种与邵氏易学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怎能出自邵雍之手?
《梅花易数》卷一又载有“八卦象列”,其中说:“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小过既济兼蛙济,是为下经三十四。完全是抄录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其卷一“八卦万物类占”,每卦的首句“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遯……”“坤为地,地雷复,地择临……”等,则是抄录《周易本义》“分宫卦凶次序”。这说明,《梅花易数》是南宋朱熹以后的著述,并非北宋邵康节先生所作。
《梅花易数》卷二有“三要灵应篇”,其序末说:“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云云,这篇序文是号为清灵子的朱虚于宝庆四年夏天作。考历代年号,“宝庆”乃南宋理宗皇帝的年号,但此年号仅用了三年,并无“宝庆四年”之说。这样饿错讹使我们十分惊讶,不敢妄言所以。
紧接其后,“三要灵应篇”的引言便排列了一个传授世系,即所谓:“是编则出于先贤先师,采世俗之语例。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陈希夷。继承得之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不知姓名者不与焉。”这个传授世系中,其他人我们不必过多考证,仅就朱虚与刘伯温而言,一看便露了马脚。朱清灵子即朱虚,序言中说是南宋理宗宝庆时人;刘伯温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宰相,乃元明之际的政治家。据此,《梅花易数》只能是明代以后人所为,并不是邵雍的著作。况且将明人刘伯温列于宋人之间,也颇有不伦不类之嫌。
《梅花易数》第三卷,首列“八卦方位之图”。如果我们将此图放在易图演的历史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第一,此图邵雍后学与王湜及朱熹《周易本义》所传邵雍“文王八卦方位”图不同。此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需自外向内看,而“文王八卦方位”图的八卦爻位,则是从内向外看,两者正相反对。其后学张行成《易通变》所传邵雍十四图,虽无后天八卦图,但其诸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顺序亦皆为自内而外。《宋元学案》所引先后天图亦是如此。这表明,《梅花易数》所列“八卦方位之图”并非邵氏原图。第二,此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在北宋并不存在。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看,直到明朝初年的赵撝谦作《六书本义》,才首次公布了阴阳鱼图,称为“天地自然河图”。
我们可以看到,赵撝谦所传“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两鱼之形,并象阴阳鱼太极图那样规范和美观。赵氏说此图“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只是恰当地表示了八卦阴阳爻画排列的情况。而阴阳鱼太极图又增加了审美的要求。这就不难推测,从粗略的赵氏之图到相当精致的阴阳鱼太极图,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也就是说,上述“八卦方位之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是更为晚出的。而它被世人所公认,被引用,并与其它易图联系在一起,创制出一个新易图,则一定是还要晚得多的事情。第三,“八卦方位之图”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
赵氏图的外围配以先天八卦方位,其目的在于以卦象中的阴阳爻象变化表现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过程,但并未画出八卦插象。“八卦方位之图”可能是依此八卦之名书写的方向,画出了八卦之象,却又将先天卦位改换成了后天卦位,这样,便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阴阳爻象与太极图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联系,也不能体现阴阳消长的法则,反映了此图作者逻辑思维的混乱。这表明,《梅花易数》中的“八卦方位之图”是明初以后很久才拼凑而成的。
此外,《梅花易数》行文的语气,也很值得怀疑。其卷一所列“观梅占”讲“康节先生偶观梅”,“牡丹占”讲“先生与客往司马公家共观牡丹”,“邻人扣门借物占”讲“先生方拥炉”,“先生令其子占之”等等。这种称邵雍为“先生”为“其”的语气,丝毫没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况,“康节”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后(元佑年间)哲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赐的谥号,岂能自称“康节先生”!“康节先生”是后世学者对邵雍的尊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梅花易数》一书错乱粗俗,不是邵康节先生所作,它只能是明代以后从事占卜的人杂抄前人占术的汇编。
二、《梅花易数》与邵雍易学天壤悬隔。
《梅花易数》纯系卜问吉凶之书,与《周易》之占天穰悬隔,乃江湖数术之类。邵雍易学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借易数推究天地万物之理,探求阴阳终始之变,属于学的范畴。学与术经纬分明,不可相提并论。
固然,《四库全书》将邵雍《皇极经世》列入术数类,但这是出于四库馆臣的门户之见。其论邵雍易学云:“邵子数学源出陈抟,于羲文周孔之易理截然异途。故尝以其术授程子,而程子不受,朱子亦称为《易》外别传,非专门研究其说者不能得其端绪。儒者或引其书以解《易》,或引《易》以解其书,适以相淆,不足以相发明也。”(《皇极经世索引提要》)从此段评论看,将其列入术数类是出于以挖几种考虑:
其一,邵子之学源于道家。亦即《皇极经世索引提要》所说:“邵子数学本于之才,之才本于穆修,修本于种放,放本陈抟。盖其术本子道家而来。”
其二,与羲文周孔之《易》不合。亦即所谓:“《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与《易》自杀相干”,“明何塘议其天以日月星辰变为寒暑昼夜,地以水火土石变为风雨雷电,涉于牵强;又议其乾不为天而为日,离不为日而为星,坤反为水,坎反为土,与伏羲之卦象大异。至近时黄宗炎、朱彝尊攻之尤力。”(同上)
其三,程朱等道学大师不予承认。亦即《提要》所说:“(朱子语录)谓康节自是《易》外别传。蔡季通之数学亦传邵氏者也,而其子沈作《洪范皇极内篇》则曰:‘以数为象则畸零而无用,《太玄》是也;以象为数则多耦而难通,《经世》是也。’是朱子师弟于此书亦在或疑之间矣。”(同上)
其四,行世之书不尽出于邵雍,此即所谓“据王湜《易学》所言,则此书实不尽出于邵子。流传既久,疑以传疑可矣”(同上)。由此可见,四库馆臣是站在经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立场来确定书目之分类的。邵雍《皇极经世》并不注解《周易》经传文义,而又依阴阳消长之理,以元、会、运、世推算兴亡治乱之迹和天地终始之变,故《四库全书》将其称为“物理之学”,而不称为“经学”,将其列入子部术数类,而不入经部易类。
如果我们冲出四库馆臣的藩篱,从易学发展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省察,那将是另一番景象。邵雍数学不因袭传统的意见,而从理论上作出了新的阐发,创立了先天易学,与张载的气学派易学和程颐理学派易学成为北宋易学的三大流派。
其实,在四库馆臣看来,邵子数学与其它术数相比,也有质的不同。《四库提要》术数类《序》云:“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渐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今古同情,趣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这是说,数学是“务究造化之源”,即探讨宇宙生成变化的根本原理的,虽“不切事而犹近理”;而占候之术虽亦见于古代经典,但流传过程中“渐失其真”,已成妖妄;其余术家如相宅相墓、命书相书、占卜之类,皆“末流猥杂”“悠谬之谈”。
邵雍数学派易学与术士方技者流天壤悬隔,不可同日而语。《四库提要》评论邵子数学“务究造化之源”,确有见地。邵雍易学不仅论数,而且论理,并以理为引导。《观物外篇》说:“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又说:“物理之学或有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这是说,讲数不可以离开理,如果离开理,则流于术。“术”,指占术一类数术。
邵雍是反对数术的。司马光评论说:“尧夫论《易》不践袭前人之说,尧夫深斥术家,盖造于理也。”(张行成《易通变》卷十二引)这些论点表明,其所谓数是同理结合在一起的,称为“理数”,如其所说:“《易》有内象,理数是也。”(同上)“理数”,指事物变化的规律性,如一分为二法,故称其为内。
邵雍认为,数的变化有其自身的法则,所以又称为“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不得更者”。数和理是统一的。程伊川评论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理方及数。”(《遗书》卷十八)这是十分中肯的。
邵雍所谓“理”,指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如阴阳消长或推移之理以及数学中的演绎法则。谢上蔡说:“尧夫见得天地万物进退消长之理,便敢做大于下学上达底事,更不施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从现在所流传下来的材料看,邵雍易学所提出的许多具体数字,虽近于数学游戏,但他确是以阴阳消长学说为中心,探究宇宙造化之源的。
第一,其八卦次序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以一分为二法说明八卦、六十四卦和世界的形成,即阴阳不断分化的过程。就世界的形成说,太极之一动则生出天,静则生出地;天分阴阳,地分刚柔;阴阳又分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此为天之四体;刚柔又分出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此为地之四体。此即《观物内篇》所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亦即《观物外篇》所说:“四象定天地之体。”由天之日月星辰又生出寒暑昼夜,由地之水火土石又生出风雨露雷。寒暑昼夜变化万物的性情形体,风雨露雷化育走飞草木,从而生出动植物,而人兼乎万物成为万物之中最聪明者。对此,《外篇》归结为“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这种学说视天地万物的形成为类与种不断分化的过程,强调层次与类属的关系,既讲宇宙发生的程序,又讲宇宙结构论的意义。
第二,以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说明宇宙万物总是处于阴阳消长的变易过程之中。照邵雍的解释,伏羲八卦方位图中,乾为天,左半圈由下向上,表示阳气生长,闢户而始生万物;坤为地,右半圈由上而下,表示阴气增长,阖户而收藏万物。离为日,起于东方;坎为月,生于西方。天地阖闢,形成春夏秋冬;日月出没,形成昼夜长短,晦朔弦望。也既是说,一年四季万物的生成变化乃阴阳二气互为消长的过程。其六十四卦方图重点讲阴阳定位,是就空间方位而言;其圆图重点讲阴阳流行,是就时间过程而言,天地人物皆处于此时空模式之中。圆图从复卦一阳生,表示一年节气变化的开始,渐次达到乾卦阳极盛;姤卦一阴始萌,渐次达到坤卦阴极盛,表示一年节气变化的终结。以后复卦一阳又复生,新的一年又接续而起,如此循环无穷。
第三,以阴阳消长法则解释宇宙和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提出了“天地有终始”的命题。《观物外篇》说:“《易》之数,穷天地始终。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意思是说,在现在的天地未产生之前有天地,现在的天地毁灭之后,也还有新的天地出现。邵雍认为,整个宇宙中的事物都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的。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了,另一个新的世界又诞生了,整个宇宙就是众多世界连续的过程。这是依据阴阳消长学说得出的一个符合辩证法的科学结论。
第四,以“先后体用”论述自己的易学体系,强调“学究天人”。邵雍提出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但他更推崇先天易学,认为先天之学为《易》之体,后天之学为《易》之用;体为根本,出于心;用为体之应用,乃心之迹。此即《观物外篇》所说:“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由于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所以二者密不可分,如果忽视后天之学的研究,就不能形成明体达用之学。他认为先天之学讲自然,后天之学讲人文,讲先天自然必须落实到后天人文,强调“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程颢曾称赞邵雍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纯一不杂”;尹和静评论:“康节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确是相当精辟的论断。
总之,邵雍易学究天人之际,穷造化之源,以探讨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和阴阳消长为其根本宗旨,对易学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宋明道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朱熹将其视为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宋史》亦将其列入《道学传》。
所有这些,都是江湖术士算命之书所不可比拟的。后世伪托邵康节之名而出现的《梅花易数》,也只不过利用了邵雍的八卦次序数、八卦方位和一些名词,如先天、后天、体用、动静而已。其实,邵雍所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是表示八卦从右到左形成的顺序,并非以一数为乾,二数为兑……八数为坤;而《梅花易数》以此为《周易》卦数,并以此起卦,占卜吉凶,同邵雍易学所谓“数”是毫不相干的。
邵雍易学的特点是讲阴阳而不讲五行,而《梅花易数》讲五行生克却不讲阴阳消长,也与邵氏之学大相径庭。至于邵雍数学精湛的理论思维,在《梅花易数》中是根本找不到的。这就显示了学与术的本质区别。
有人可能会说,邵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岂不是占算大师?固然,依史志所载,邵雍确能推论事物发展的趋势,但他预知事物变化的动向,所依据的是“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并非其它算命之术。《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说:“先是于天津桥上闻杜鹃声,先生惨然不乐,曰:不二年南士当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问其故。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得其先者也。”这是依南北地气互有盛衰,推论南人将入相掌权。此说并不科学,但他认为其预言是依据阴阳互为消长的规律,而不是靠神秘的启示。《百源学案》接着说:“横渠问疾论命。
先生曰:天命则已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天命”指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世俗之命”,指人事的吉凶祸福、贫贱寿夭。邵雍反对推算人之命运的数术,故云“不知”。又说,邵雍能预知洛阳牡丹之盛,其根据是:“见根拨而知花之高下者为上,见枝叶而知者次之,见蓓蕾而知者下也。”(同上)这是依据牡丹生长的规律推知其开花的情况,就像人们刻水仙花,能控制它在大年初一盛开一样。此种预言,无可非议。这种依据事物发展规律推论事物变化趋势的预测,同《梅花易数》的江湖占术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宋史·邵雍传》明确提出:“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测屡中者。”世俗占卜之流与邵雍易学不可同日而语。
三、偶然性的联系得不出必然的判断。
《梅花易数》卷二之《三要灵应篇序》曰:“吉凶悔吝有其数,然吾预知之,何道与?必曰:求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又说:“易之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所以《梅花易数》又自称为“心易”,如卷二第一篇称为“心易占卜玄机”,第六篇则称为“八卦心易”,并明确提出:“占卜之道,要变通得变通,得变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
就是说,占卜之道,全在一心。具体到起卦,就是完全凭借占卜之人灵机一动,随心所欲而确定的。《梅花易数》随意性起卦,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种:
1,年月日时起卦:以年月日数为上卦,年月日数再加时数为下卦。因为经卦为八,其余以八除,所余之数即为此卦。如书中所列“观梅占”: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见二雀争枝坠地。辰年为5数,十二月为12数,十七查为17数,共34数,除去四八32数,尚余2数,二即兑为上卦;年月日数再加申时数,总为43数,除去五八40数,尚余3数,三即离为挖卦。这样便得到一个上为兑下为离的革卦。
2,物数起卦:凡见到可数之物,即以此数起作上卦,加时数起作下卦。
3,声音起卦:凡听到声音,数得几声,起作上卦,加时数配作下卦。如听到间断之声,也可以用前面声数起作上卦,后面声数起作下卦。
4,字数起卦:凡见字数,如为偶数,则上下平分,一半为上卦一半为下卦;如为奇数,则少一字为上卦,多一字为下卦,取清轻者为天,浊重者为地之义。如字数多,直接以字数起卦;字数少,则以字之笔画起卦。如一个字,则左边笔画为上卦,右边笔画为下卦。⑸人物起卦:凡见人或物,以人物为上卦,其方位为下卦,如此等等。
由上述种种起卦方法,我们看到《梅花易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耳闻目睹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选取其中某一两个方面,随意地联结为一个虚假的事物,并企图以此为前提,推论出真实可靠、确定无疑的结论。这样《梅花易数》就把自己预知吉凶祸福的方法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殊不知,虚假的前提是推不出确定真实的结论的。
“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讲的让敌人依据虚假的前提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的道理。
不仅如此,逻辑常识和占筮史实告诉我们,虚假的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结论,根据同样一卦,不同的占卜者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抛开其它占筮体例,仅就虞翻易学而言,求得某卦,就可以通过卦变说引出另外的一卦,通过旁通说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卦,然后再与互体、半象等说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取象,便可随意选取其中某些卦象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各种判断。
王充《论衡》和《北堂书钞》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事件,讲的是孔子门人子贡作为使者到各地游说,到了归期仍然不见回来。于是孔子占了一卦,得到鼎卦,以变爻九四占断,其爻辞为“鼎折足”。孔子的门人们依据这个爻辞都说:“卦中说没有足,看来,子贡暂时回不来了。”惟独颜回笑而不语。孔子问其故,颜回答道:“子贡一定会回来,即使没有足,也会乘船回来。”颜回之所以说“乘船”,是因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为木。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卦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讲出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就清楚地表明,依据《易》卦这种虚假的前提,推不出确定的结论。因而《梅花易数》仅凭随意拼凑的前提进行推论,其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梅花易数》的作者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种占卜方法不可避免的失误,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他们认为,仅有内卦(指所起之卦)不行,还必须参考外卦(指占卦时所闻所见之物象的感应)。“不知合内外卦为断……则鲜见其有验者”;“内卦不可以无外卦,外卦不可无内卦。占卜之精者,无非合内外之道也”(《内外论》)。
因此《梅花易数》又提出了“三要十应”的方法。“三要”即运用耳目心思三者之要。“应”,即外物之感应。认为依据所见所闻皆可作出判断,见吉则吉,见凶则凶。诸如云开见日,事必增辉;烟雾障光,物当失色;月忽当雨,宜近清光;雨乍沾衣,可蒙恩泽;二男二女,重婚之义;一僧一道,独处之端;逢猎者,得野外之财,见渔夫,有水边之利;乌鸦报灾,花鹊报喜,犬争恐招盗贼,鸡斗主有喧争……如此等等,《梅花易数》称之为“事事相关,物物相应,是以验吾占卦之切要也”(《动静》)。
《梅花易数》此番议论,自以为得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迷惑求卜者的障眼之法。从上述事例我们看到,其借以推断吉凶祸福的应验之象,无非是占卜之时偶然碰到的一些现象,企图依此作出即兴的必然性判断。而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偶然的联系得不出必然性的判断。因而,依据《梅花易数》的方法作出论断,也是靠不住的。
四、五行生克不能正确解释事物之间真实而繁杂的关系。
按照《梅花易数》的说法,占卜吉凶晦吝的关键,“在于区分体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克比和之理”(《八卦心易体用诀》)。就是说,确定体卦、用卦、互轧、变卦之后,即以五行生克之理,判断其吉凶祸福。个体原则可以概括为:“体克用,诸事吉;用克体,诸事凶。体生用,有耗失之患;用生体,有进益之喜。体用比和,则百事顺遂。”“体党多而体势盛,用党多则体势衰”,“体盛则吉,体衰则凶。”(《体用总诀》)“五行生克”说是《梅花易数》推论判断、占算吉凶的主要理论支柱。
所谓五行生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创立的一种理论模式。从汉朝开始,易学家们将此种学说引入易学,用来解说《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经过西汉易学大师京房等人的阐发,后来成了算命术的一大理论基础。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五行生克是否能够概括世界上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事物的相互关系?
我们知道,五行生克说是以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的性能或作用来说明其相互关系的。它仅仅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的属性、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粗浅认识。而大千世界的客观事物,既区分为不同的领域、类别和层次,又有相当繁杂的关系。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易传》,就讲到了相互对待的事物之间的相摩、相荡、相推、相揉、相攻、相取、相感、相易等关系,更不要说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进化和人类社会相互资助、相互融合以及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关系了。
即使同一种物质,其性质也是多方面的。以水为例,它不仅仅具有“润下”的性能。就直观而言,水性柔弱,却可以滴水穿石,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盛于圆则圆,盛于方则方。水又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热则成汽,寒则凝冰。水还具有不息不止、循序渐进的性质。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孟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就微观而言,水在4℃的温度下比重最大;在一个标准大气压,水的沸点为100℃;水又区分为纯水、重水、双氧水,纯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水分解则变成氢和氧,等等,等等。因此,五行生克并不能概括世界万物的复杂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五行生克说解释世界,也只能是以偏概全,得出片面以至错误的结论,歪曲世界及其事物的本来面貌。
同时,以五行生克推论人事活动,预知未来之事的吉凶,也是违背逻辑推理法则的。逻辑推理有一个基本法则,就是同类同质的事物可以相推,而异类异质不能相推。五行生克是以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的机械性能为基础的,属于物理学范围,而人类是高级动物,有意识,有思想,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并且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家庭、单位、民族、阶级、政党把人类既区分为各种集团,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事活动属于社会学范围,不同的科学范围,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类别乃至不同的层次之间,都有质的差别。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矛盾和运动规律,不能互相归结。把适用某一运动形式的规律,运用于其它运动形式,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同样,以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也是不能推论人事活动的。可是,《梅花易数》却即不顾辩证思维方法,又不顾形式逻辑规则,硬将这种不同范围、不同运动形式的东西放在一起,加以推论。此种推断,既然犯了异类相推的逻辑错误,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它只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并不能预测吉凶后果。所以,把《梅花易数》之类的算命术视为一种科学的预测,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本文作者作者:郑万耕,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本文原为繁体,由郭彧录自《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附录——朱伯崑先生之谈:
宋代易学哲学家邵雍,乃宋易象数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因为主“象生数”,其易学被称为“数学”。因而《四库》的编者,将其著作列入“数术”类。其实,邵雍的易学,谈数,并非江湖数术之流。他是一位儒家学者,以继承孔孟之志为己任,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其所穷之理,一是“物理”,二是“性命之理”,后者指人生之哲理。其论数,以理为引导。他说:“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其理也。”(《观物外篇》)又说:“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同上)他所谓的理,指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如阴阳消长或推移之理以及数学中的演绎法则。认为谈数而不及理,则流于“术”。他是反对数术的。
他预知未来事物变化的动向,所依据的是阴阳消长的规律,不是其他。据说,他于天桥上闻杜鹃声,推测南人将入相掌权,天下自此多事。他的根据是,南北之地气,互为盛衰。今南方地气北移,禽鸟得地气之先,暗示南人将得势。此说,并非科学,而且具有神秘主义运气说的色彩。但他认为其预言是依据阴阳互为消长的规律,而不是靠鬼神的启示。
据说,他能预知洛阳牡丹之盛衰,其根据是:“见根拨而知花之高下者,为上;见枝叶而知者次之;见蓓蕾而知者下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此是依据牡丹生长的规律预知其开花的日期。此种预言,是无可非议的。总之,他将儒家的人文主义占筮观,引向依物理推理事物发展趋向的道路。这同后来江湖数术伪托邵雍之名所炮制的《梅花易数》有天壤之别。故明末科学家和象数之学的代表方以智,将邵雍视为同张衡、祖冲之、一行等齐名的人物,并斥责江湖数术说:“其言象数者,类流小术,支离附会,未复其真,又宜生厌也。”(《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其所说的“类流小术”,即其父方孔炤所批评的“矜方占验,则流为术数耳”(《时论合编?三易考约》)。可见,宋明时期易学中象数之学的代表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江湖派的算命术,就此而言,亦是对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的发扬。(摘录自《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一文,载《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
丘亮辉先生之谈:
邵雍的易学,提出先天卦序说,将八卦分别配上八个数字,其目的是用来标明画卦过程从右到左的顺序。可是在《梅花易数》一书中,则成了以其卦数占问吉凶的工具。对这两种传统,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在研究中,便会迷失方向。
(摘录自《简评周易与占术》一文,载《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